
電視台如要翻拍《書劍恩仇錄》,某書店服務員是現成的最佳人選,她比年輕時的余安安更像香香公主,金庸先生看見她,恐怕也會說:「就是她!香香公主就是她!」

「心安理得,海闊天空」是梁啟超的名言雋語。筆者從解讀《射鵰英雄傳》學會要用「調轉」的方式來更好領悟其中意義。原來得到道理方能安心,才可感嘆天空海闊,自由自在。

蘇軾的生平是創意的一生,將中國文化的創意精神發揮至頂峰,不論順境逆境,都流露了豁達的一面。

「一個創作者最重要的事,就是有人欣賞你,而去追看你的作品。作家在香港來說,不會太多人認識。viuTV正在播映的電視劇《已讀不回》改編自我的著作,但觀眾只會記着劇中角色,不會記着我這位原著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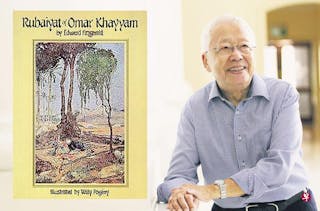
一般譯詩,由一種語言轉譯為另一種,如果重意不重詞,難度仍未算極緻,像《魯拜集》過去就有郭沫若與孫毓棠的全譯本,但他們都是用自由體翻譯的。

查良鏞少年時已在外交上努力學習而且攻讀相關學校學科,亦曾在內戰後的外交部任職過一段短時間,他是否欲效法梁任公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樂見《百年巨匠》紀錄片拍攝饒宗頤教授的生平、事蹟,讓更多人能認識到才情橫溢、學藝雙攜的饒公,同時借助紀錄片傳誦他深厚的學養內涵、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堅定決心。

給香港中學生講元曲是不容易的。太難不行,知識點少了也不行。而且字數要求在千字左右,所謂字字是乾貨也。記得網友也每每想聽一點元曲的故事,故采之以饗讀者。

前幾天,接到何福仁的電郵。傳來10月8日西西獲得第六屆紐曼華語文學獎(詩歌獎)的消息。她是這個獎的第三位女性獲獎者,也是香港首個獲獎作家。

緣份亦是當年被稱為民國才女的林徽因做過大公報副刊編輯,或因而使查良鏞走上同一生涯路途。

曹乃謙與賈樟柯同出道於荒野本質的山西,究竟他們心裏的文化特質,怎樣衝破地域限制,不受困於貧窮落後荒野,其感染力成功滲透到無遠弗屆,達至遙遠的瑞典和巴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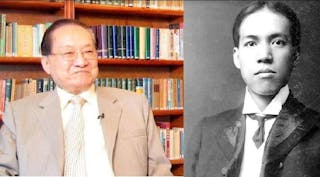
金庸將梁思成與林徽因的事蹟寫成是為國為民的大俠郭靖和黃蓉,梁啟超父子及媳婦在查良鏞心中的地位定必非同尋常。

推動學生的人格教育,是鍾玲的目標;培養對社會有承擔,富有人文素養的學生,是鍾玲的理想。

今次筆者解讀《射鵰》謎團後發現原來小說包含了兩個動人心弦的英雄故事。看到梁林面對苦難時,筆者知道是真實歷史而感同身受,又會為郭黃排除萬難,每次都有驚無險,大步過關而歡呼喝采。

哪一個名稱是《紅樓夢》最真確的稱呼?我個人認為,糾纏幾個或虛或實的名字,本身就沒什麼大意義。

司馬長風等知識分子,痛心中國文化受摧殘,又嚮往西方的自由民主,因此友聯的刊物,就成了他們散播理念的平台,《中國學生周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人心,是可以統計歸納的。通曉行為心理學,讓他它成為你最強的職場武器。

論到香港文學的價值在哪裏,她與香港歷史和社會現實構成怎樣弔詭的關係,足證文學的多元價值,香港的本土文學,既可作跨域理解,為香港人說故事,為香港編寫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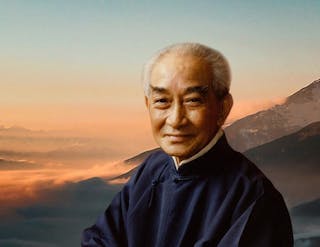
「不二門中有髮僧,聰明絕頂是無能。此身不上如來座,收拾河山亦要人。」南懷瑾這首詩,也能說明他不止心在普及經典,亦心繫現實社會政治。

段正淳能渡己,但不能渡人。自己的快樂,別人卻哀痛,所以他的品格,亦如他的武功一樣,至死亦未及第一流境界。不過,在濁世之中,仍不失為一號人物,而成為濁世佳公子的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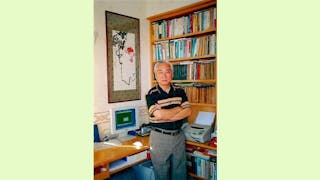
香港60、70年代是讀舊書的好時年,大陸台灣的文學禁書盡在香港,許定銘跑勻大小書店搜購,皓首窮經,終於修成正果,成為「書神」。

蘇東坡有的是那樣體貼的賢妻,能在未有需要時已為將來有需要時籌謀,「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真是世情的絕配了。

Balli Kaur Jaswal指出,國際知名印度裔作家的作品,多從男性角度出發,忽視了女性在爭取自由時,面對的不只是東西文化和年齡代溝的障礙,還有男作家不能感同身受的隱形性別歧視。

一眾作家寫西西,下筆不見沉重,是與西西作品遙遙呼應了。

「第一部小說《龍頭鳳尾》裏的主要人物是江湖人物,而新書《龍‧續》的主要人物是警察。大家可能有人知道我喜歡寫三部曲,換然之,第一部是黑,第二部是白,那第三部就是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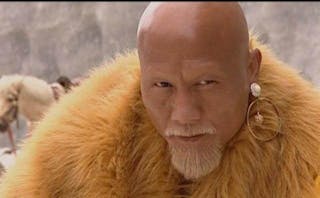
好人只有一個「好人」的模樣,壞人的壞法便千變萬化。壞人中有大奸大惡,有小奸小惡;有陰險偽善,有自尊自大,霸道張狂;有由正入邪,有由邪入正。

18年前李歐梵教授和李玉瑩女士結婚時,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寫給他倆的一首七律,有「歐風美雨幾經年,一笑拈花出梵天」之句,可謂準確預言了兩人的姻緣。

人生不易,以最深切的感受,參透人生的苦楚。

法國知識分子真的沒落了嗎?從法國國內而言,關於知識分子的詰問不可謂不多,但是,此話題關鍵並非在於提出問題,當今的法國,知識界缺乏眾望所歸的思想領袖乃是不爭的事實。

秋風清,秋月明,葉落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見相親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