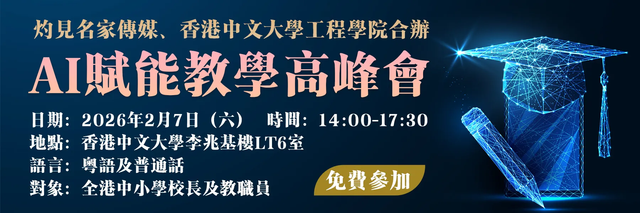2026年冬季達沃斯論壇傳出來幾個強烈得「刺腦」的信號都指向當今國際政治的本質性變化。作為一個西方的論壇,達沃斯每年討論的要不就是西方國家整體面臨的內部問題,要不就是西方國家整體面臨的國際問題。在過去的很多年裏,論壇的討論愈來愈集中在地緣政治的變遷。
但在今年的論壇上,幾乎所有重要的爭論都發生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間,圍繞着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這和從前那麼多年往往圍繞着俄羅斯的烏克蘭戰爭或者中國的崛起等情形已經截然不同。之所以截然不同,是因為這場論壇「終於」宣告了一個長時代的結束,但卻未曾告知人們一個什麼樣的新時代將到來。世界因此進入了一個對於未來的「無知」狀態。有「無知」就有不確定性,就會有憂慮和恐懼。
舊世界與秩序已經倒塌
人們可以簡單地把這裏所說的「舊世界」和「舊秩序」理解成為二戰以後的世界和秩序。二戰迄今過了四分之三世紀,這個「舊世界」是各國大多數人口都生活過來的世界。不過,舊秩序則是西方世界塑造的,西方自己是這樣認為的,非西方國家的人們也是這樣認為的。因此,今天舊世界倒塌的根本原因首先在於西方世界的倒塌。
正如近代以來,西方世界憑藉其佔據絕對優勢的話語權,爲非西方世界構造了諸多區域概念,但實際上,「西方」的概念也是西方世界自己本身構造出來的。西方這一概念有其實然的一面,更有其虛構的一面。
一方面,西方是真實的。一是因爲這個群體的國家有基於共同的宗教之上的文明和文化,「文明的衝突」的概念就意味着西方這個群體的宗教性質。二是這個群體包括最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就是發達的西方,就是說,這個群體具有共同的經濟利益。三是這個群體發展出了差不多的政治體系,即民主,也正因為這樣,長期以來西方簡單地把世界上的政治體系分為民主和非民主兩個陣營。
但是,無論從理論上還是經驗層面,西方的概念更是虛構的。

一是西方實際上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虛構。正是因爲上述共同性,西方纔有條件構造了西方的概念。不過,西方的概念至多也就是英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創造的概念——想象的共同體。這是一種想象,這種想象的表象掩蓋了太多的不同。宗教的不同是不用言說的事實,「資本主義的變種」指向了不同的經濟體系和利益,而在西方這個群體內,並不能找到一個一模一樣的民主模式。對非西方國家來說,正是因為西方的故事講得好,人們普遍地把這個「想象的共同體」視爲是事實了。
二是西方的存在取決於非西方的存在,尤其是一個敵人的存在。作為宗教文明的西方,其內核便是天使和惡魔的兩分法。表現在世俗世界中的國際政治,便是西方和非西方、朋友和敵人、正義力量和邪惡力量等的對立。尋找敵人或者塑造假想敵,是西方文明的內在部分。
今天,傳統所謂的西方概念已經轟然倒塌。倒塌的原因極其簡單,一是因為西方這個群體內部的共同性已經掩蓋不了其內部的差異性,二是因為非西方世界的變化。西方內部的差異性使得這個群體中的不同國家和非西方世界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西方和非西方的邊界變得愈來愈模糊。
新世界已經來臨 新秩序卻未有共識
不管人們喜歡與否,新世界已經來臨,但新秩序還沒有出現。從這次達沃斯論壇來看,在西方這個群體中,愈來愈多的國家似乎已經準備好向「舊世界」告別。但是,糟糕的是告別了這個「舊世界」之後,人們要走向一個怎樣的新世界?因爲沒有任何確定性,這是人們最恐懼的。
新秩序是怎樣的?無論大國還是中等國家,對此都沒有任何共識,更不用說那些對局勢只能「無動於衷」和「搭便車」的較小國家了。沒有秩序,所謂的「新世界」只能是一個「無政府」狀態,而「無政府」狀態是人類所不能承受的。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塑造一個新秩序,是根據人類所擁有的理念和價值觀來構建一個新秩序,還是接受一個「自然」形成的新秩序?如果是前者,那麼就需要至少三個前提,一是存在着各國都能夠接受的理念和價值觀;二是有能力構建這個秩序的大國或者幾個大國都必須接受這些價值觀;三是其它國家尤其是中等國家能夠接受這些大國的領導角色。
不過,現實是這些基本條件都不存在。首先,舊秩序的倒塌是體現舊秩序價值觀的倒塌;其次,沒有一個大國或者幾個大國有能力構造新秩序,因為各大國都在轉向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即我們所說的國際秩序「封建化」;再者,世界缺失能夠讓中等國家或者較小國家接受的領導型大國。因此,一個「自然」形成的秩序變得更有可能,眼下也就是一個達爾文式的「叢林世界」。

強權再次瓜分世界?
「瓜分世界」已經取代了「大國政治的悲劇」。自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國際政治的主導話語便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國爭奪霸權導致世界大戰。這個理論的依據是,人類自16世紀開啟以來,迄今已經發生了16次權力轉移,即權力從一個現存大國轉移到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12次霸權爭奪戰爭,而只有4次實現了和平轉移。這個理論也認為,下一次霸權爭奪戰必然發生在世界的「老大」和「老二」之間,即美國和中國之間。但從經驗看,修昔底德陷阱並沒有發生,今天的大國關係已經演變成爲再次聯手瓜分世界了。
人們只能說,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國失靈了。這並不難理解,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文明的邏輯,而非中國文明的邏輯。
大國的「瓜分世界」是從西方文明開始的。先是俄羅斯,再是美國,而其他在西方邏輯內的中等國家也在躍躍欲試。俄羅斯的領土擴張以抵抗北約的擴張爲理由。近代以來,俄羅斯一直處於不斷的擴張之中。蘇聯本來就是俄羅斯擴張的結果。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變小了。但西方並沒有饒過俄羅斯,因爲西方相信如果不能「絞殺」俄羅斯,俄羅斯遲早要再次走上擴張的道路。因此,蘇聯解體之後,以北約爲首的西方一直沒有停止過擴張,擠佔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空間,使得俄羅斯變得愈來愈沒有安全感。也就是說,北約對俄羅斯的擠壓適得其反,導致了俄羅斯這個戰鬥民族的絕地反擊。這是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的原因,也是俄羅斯發動俄烏戰爭的原因。不管俄羅斯的擴張是基於什麼樣的「正當」理由,但客觀的結果就是在列強中率先開始再次「瓜分世界」。
今天的特朗普則緊隨其後。較之俄羅斯,特朗普的美國正在開啟近代以來曾經盛行但後來被世界所拋棄的兩種主義,即新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特朗普屬於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即目的證明手段正確。對拉丁美洲,特朗普實行的是新殖民地主義,最顯著地表現在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政策。
很自然,委內瑞拉絕對不會是美國唯一一個新殖民地主義目標,很多拉美國家似乎都做好了心理準備。對世界更多的地方,特朗普實行的則是帝國主義,並且是毫不掩飾的傳統帝國主義。特朗普第二次執政之後,很快把「墨西哥灣」改成「美國灣」,要再次控制巴拿馬運河,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一個新州。最近特朗普對控制格陵蘭島的戲劇更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

特朗普瓜分世界的動力來源
無論是新殖民地主義還是帝國主義,特朗普「瓜分世界」的動力來自兩個因素。
一是美國的擴張本質。美國建國之後,一直處於擴張之中,從來沒有間斷過。只是二戰之後,美國的擴張變得比較精緻了,用一個「好的故事」來擴張。如果不是擴張過度,那麼就不會有今天人們所說的特朗普「收縮」。
不過,「收縮」的概念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質。從表面上看,特朗普新現實主義把美國的戰略重點從全球轉移到「國內—周邊—後院」,但實際上則不是。更精確地說,人們可以把這一戰略轉移理解成爲「調整和鞏固」。特朗普只是調整了擴張的方式,而沒有改變擴張的本質。並且這種調整是爲了鞏固美國的內部、周邊和後院,以便將來更強有力的擴張。
再者,全球面的「收縮」也具有欺騙性。特朗普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離岸平衡」,即利用美國的盟友進行遠程控制。對特朗普來說,「離岸平衡」可以起到兩個作用,第一,讓美國的盟友承擔更多的責任;第二,大大減少美國本身的成本。
二是特朗普遏制不了俄羅斯的擴張,便選擇不甘落後,轉而進行更加激進的擴張。儘管俄烏戰爭是北約本身擴張的結果,但西方從一開始還是想遏制俄羅斯的擴張。這構成了這些年來西方和俄羅斯關係的主線。
特朗普第二次執政之後,開始的時候也是想結束俄烏戰爭的。但不管怎樣的努力,都沒有任何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特朗普轉而聚焦自己的擴張。這也不難理解。近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的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殖民地主義還是帝國主義,都具有競爭性的,即各列強之間的競爭。近代早期,更多的國家參與殖民地義和帝國主義。儘管今天參與的國家主要限於俄羅斯和美國,但這並沒有改變競爭的本質。

拋棄歐洲來改變歐洲
「瓜分世界」對大國來說或許是其本質所驅使,但對中小國家來說則是一個悲哀的故事。當較小國家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中等國家就有了強烈的反應。儘管今天是中等國家,但曾幾何時,他們也是近代以來的列強,曾經瓜分過世界,對瓜分世界擁有切身的經歷,知道列強瓜分世界的時候會發生什麼。
毫無疑問,「中等國家聯合起來」便是這次達沃斯論壇傳達出來的最強烈的呼籲。他們不能坐以待斃,而是要聯合,主動抵抗強權,塑造國際秩序,而非一個接受秩序的被動角色。
不過,儘管言詞很美好,意願很強烈,但現實則很冷酷。無論是歐洲還是其他西方中等國家,要追求自主的聲音這些年來一直沒有中斷過,也不乏真誠的嘗試,但並沒有任何可見的效果。法國總統馬克龍曾經多次說,北約的腦死亡。但經驗地看,腦死亡的不僅僅是北約,而是整個歐洲。
有一點特朗普說得很對,二戰以後,美國為維持和「保護」西方作出了「不計較成本」的貢獻。但這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這些國家高度依賴美國,並且視美國的保護爲當然,從而愈來愈沒有保衛自身的能力;二是這些國家沒有足夠的貢獻,使美國自身的地位難以為繼。從這個角度來說,儘管所有這些中等國家視美國「背叛」了西方,但從一個非西方的角度來說,特朗普這樣做便是要以壯士斷腕的方式來拯救整個西方。特朗普指責歐洲已經變得「面目全非」,指責歐洲的文化墮落,很顯然已經把歐洲的危機提升到文明的高度。
特朗普強調美國不會拋棄西方,但很顯然他想盡快拋棄一個左派的歐洲,而扶植一個右派的歐洲。這個目標是否會成功取決於至少兩個因素。一是西方本身是否會獨立思考。因為過度依賴美國,久而久之,很多西方國家失去的知識上的獨立思考能力——跟隨美國走的傳統依然是歐洲的主流。
二是美歐之間的關係如何演變。二戰以後,美國可以拉着歐洲來改變歐洲。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和冷戰結束後的美歐關係就是如此。但是,美國不能夠透過拋棄歐洲來改變歐洲。最悲哀的事情是,儘管特朗普如此對待歐洲,但對歐洲來說,最恐懼的便是被美國所拋棄。美歐關係如何發展決定了傳統西方是否會再現。
〈中國與新世界〉二之一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