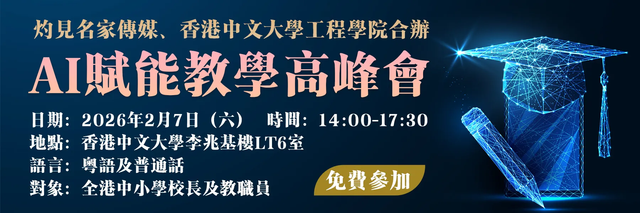我所感知的李天命教授,其貢獻也許並不在於建立一套宏大的哲學體系,而在於他改變了我們如何思考。他的「思想方法學」,不教人背誦定律,也不訓練辯論技巧,但要求我們對語言保持警覺,對推論保持紀律,對空話保持不耐煩。他重新界定「謬誤」為一種思維方用式的錯誤,而非單純推論或事實錯誤,並強調語言若不先釐清,真假與對錯根本無從談起。他以「智劍」作比喻,是態度,是為了不被假深刻、假問題與假論證所蒙蔽。正因如此,他的思方不依賴特定理論,也不隨學術潮流過時,而是直接嵌入我們的思考習慣之中,成為一套「辟邪劍法」。
我是其中一個盤腿而坐的學生
在中大一年班下學期上他的課,那是個現在已很難想像的畫面:偌大的演講廳,座位早已坐滿,後排站滿人,走道上、出口旁、甚至地板上,都坐着學生。課程應該不是必修的,卻長期一位難求,如此轟動,敢情也因為教授比較手鬆!?
大學我主修的是歷史和後來的政治學。那個年代,李教授的課被歸類為通識教育,任何學院學系的學生都可以修讀。現在回看,這是一個極其難得、甚至有點奢侈的制度安排。歷史與政治學給我的,是理論、模型、假說;它們當然重要,但說到底,大多是暫時性的知識。新資料的出現、新理論的提出,原本看似牢不可破的推導,隨時會被修正,甚至被推翻。但李老師教的超越這一類東西。
我有個清晰的記憶:在修讀他的GEE111、翻過他的書之後,我第一次覺得自己開始「思考」了──不是背誦,不是死板推導,不是沿着既有論述隨機漫步,而是一步一推演,檢視前提,拆解謬誤,辨認同義反覆與空洞陳述。今天回想,雖然我得分不高,也已不能完整複述他某一個具體模型,但我可以肯定,他的方法已成為我思想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在運轉。
這種印記,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自覺地顯現。
有一次,我與同學一起去聽公共政策的某場爭論,當下便覺得那是一場娛樂秀。從李老師的視角出發,聽政治人物的發言,實在太有趣了:A等於A、倒果為因、來回兜圈的循環論證,一句接一句,聽着聽着,不禁「噗嗤」地笑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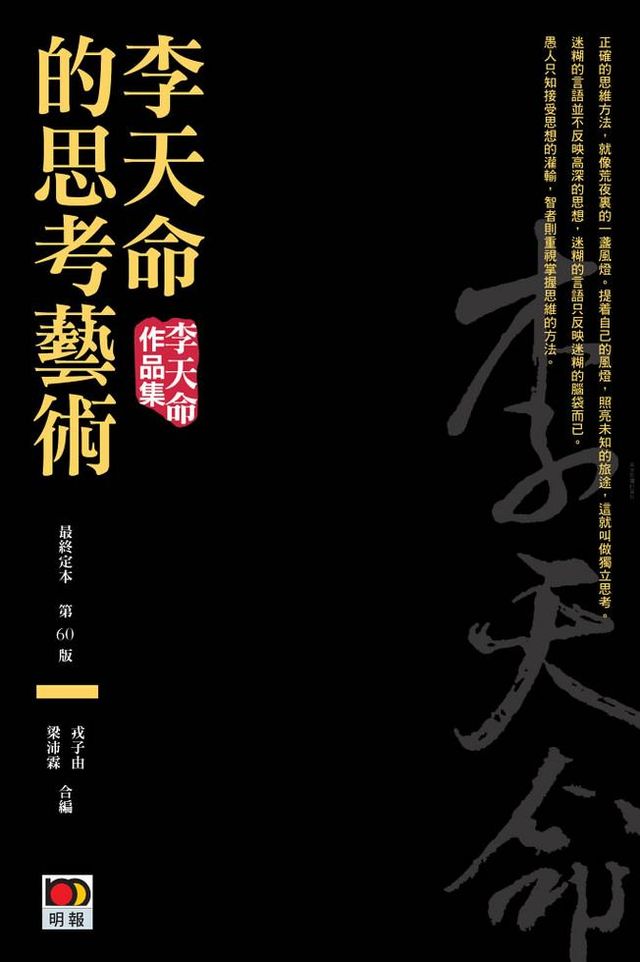
沒教我投資 卻教我拆穿把戲
畢業後,我投身金融行業。跟公共政策的分析相比,金融分析相對不那麼「空轉」;數字、結果與代價,通常來得更直接,但也不盡然。其中,可能是思方劍的影響,我始終對技術分析保持距離。我不知道李老師有否炒股,也不知道他會如何看待技術分析,但我有時會幻想一個場景:若有一位技術分析師,試圖用「頭肩底」、「阻力位」之類的圖形波浪來游說他買入某隻股票,結果可能會換來「小李飛刀」!
2020年我莫名其妙地買下了《李天命的思考藝術》(2018年版,已是第68版),和《不定名》(2020年版)。當時重讀時,圈下了以下的句子:「人生在世,必須有點幽默的智慧⋯⋯幽默笑死自大,幽默笑死自卑」。
多年過去,思方劍破空之聲依然清晰。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