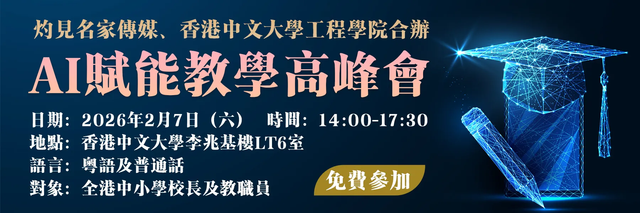如果從這些方面來檢視中國學者所處的環境,那麼人們還是可以看出很多問題來的。中國學者所面臨的環境很複雜,但必然包括如下幾個情況,一是「帽子」,二是「級別」,三是「位置」,四是「榮譽」,五是「有組織的研究」。所有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對他們的科研產生着負面、甚至是致命的影響。
帽子
世界範圍內,很難找得到像中國那樣的學界擁有如此眾多的「帽子」。中國有國家層面的「帽子」,也有各級政府和各個城市給的「帽子」。有人說,幾乎所有的「江」「河」「山」「海」的名稱都被用完了,因為「帽子」往往是以這些名稱來命名的。
類似的「帽子」西方也有,但很少,至多是一些「講席教授」之類的東西。不過,西方的「講席教授」並不是中國的「帽子」,因為在西方這個「帽子」也就是「帽子」,僅此而已。但在中國,「帽子」是具有巨大的含金量的,不同的「帽子」,不同的含金量。因此,為了爭取一頂「帽子」,人們可以花費巨大的精力,並且透過無所不用的手段。
級別
學界本來可以是最平等的地方,因為知識沒有級別,人人在知識面前平等。但在中國的體制內,級別森嚴。教授分成很多級別,即使是正教授中也分出諸多級別。如果從資深的角度或者教授們所取得的科研水平而言,級別無可非議。但問題在於,人們往往把這種級別和知識級別混淆起來,以為教授愈資深,他們的知識級別愈高。
中國學界的角角落落被各種「學閥」所控制,各種「團團夥夥」內部高度級別化,猶如從前的企業。年輕學者把這些「學閥」視為是「老闆」。知識界的競爭基本上表現為學閥之間的競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我們的鄰居日本,也是東亞文化,也有類似的學閥現象,但日本的學閥和中國的學閥運行方式不同。
在日本,學閥負責挑選接班人的時候,總是能夠把他(她)視為是最優秀的人挑選出來,以維護學閥的傳承性質。在中國學界,學閥往往是「武大郎開店」,為了保持其終身的影響力,他(她)絕對不會把最優秀的人挑選出來,因此,一個學閥一旦過去,那個團夥也就「樹倒猢猻散」,很少有傳承性,而沒有傳承性,也就沒有積累性質。

位置
「位置」和「帽子」不一樣,儘管它們之間也有重合的地方。中國學界基本上還是一個行政主導的體制,因為不同的位置決定了可獲得資源的多少。西方的大學很是平等,行政(系主任等)工作是服務和奉獻,因此大家可以輪流當。但中國的學界則不然,大家可以為了一個位置爭得頭破血流。
當代,很多從海外學成回來的學者往往被給予一個行政位置,這倒不是因為這些回來的學者的初心,而是客觀現實的需要,因為如果沒有一個位置,人們就分配不到相應的資源,為了獲得相應的資源,人們必須去爭得一個位置。問題在於,一旦有了位置,「屁股指揮腦袋」原則就開始發揮作用,這些位置上的人們不再是研究者,而儼然是「官員」了,他們的研究也往往被荒廢了。
榮譽
「榮譽」是誰都想要的,任何社會都是如此。人是社會的人,誰都想得到人們的尊重。但問題是「榮譽」如何體現?上述「帽子」「位置」都被視為是「榮譽」的載體。不過,正如前面所討論的,一旦「榮譽」和這些載體合二而一,那麼不再是榮譽了,而是利益了。
對很多學者來說,爭取榮譽也就是爭取利益,這是一個過程。當「位置」「級別」「榮譽」和利益緊密結合起來的時候,就會產生使得任何一個科學家都難以抵制的誘惑。不過,這也與當代社會對「榮譽」的看法也是有關係的。中國具有「士農工商」的傳統,「士」這個階層也是備受尊重的階層。因此,人們說,中國是一個尊重知識的社會。但現在這一文化似乎蕩然無存了。社會變得極其勢利和功利,如果不能帶來利益,榮譽一分不值。學者們對自己榮譽的不尊重和社會對學者榮譽的看輕互相強化,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有組織的科研
此外,「有組織的科研」對研究者們也是有深刻影響的。在當代,愈來愈多的國家,科研愈來愈呈現為「有組織的科研」。很多國家希望通過有組織的研究來實現科學技術領域的趕超,但即使是在發達國家,例如美國,科研也表現為高度的組織性質。這是當代科研的性質所決定的,但「有組織的科研」的目的性和工具性都很強,因為所從事的研究就是為了實現國家或者組織所設定的目標。
因此,研究者們的興趣很少是自己的興趣,或者說自己的興趣要服從於組織或者國家的「興趣」。而正如前面所說的,沒有自己的興趣,研究者們的研究大多都是工具性的,也就是「生活」和日常工作而已。
再者,「有組織的科研」大都是應用性質的,因為所謂的「趕超」就是前面有了具體的目標,這些目標大都是應用技術。此外,有組織的科研也往往導致一個思想市場的缺失。在有組織的科研裏面,不僅不容許存在不同的思想,更要求思想的統一,因為只有大家思想統一了,才能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儘管共同的目標甚至共同的思想並不必然影響學術思想的不同,但人是有惰性的,在沒有足夠思想刺激的情況下,很容易和其他人趨同,即自覺地放棄自己的思維。

(Shutterstock)
更深層次的問題:功利主義的教育與文化土壤
更進一步,在中國的環境裏,還存在一個廣義上的「組織」。人們可以說每一個個體的一生都是處於有組織的科研的模式裏。這裏的「組織」包括家庭、幼兒園、小學、中學、高中、大學等,所有這些「組織」都在深刻影響着個體的興趣。很多人說有自己的興趣,但實際上並不是他們自己的興趣,而是他們的家長、老師和教授所給予的他們的興趣。學生厭學和學者厭研都是沒有找到自己的真正興趣的結果。
如果人們覺得這些影響着中國學者去從事可以獲得諾獎的研究,那麼人們也可以明瞭今後所需要的改革,那就是去帽子、去級別、去行政化,回歸榮譽,處理好有組織科研和個性之間的平衡等。問題在於,對所有這些「存在」所產生的弊端也是路人皆知的,並且經常有人在討論,有關方面也經常試圖進行一些改革,但是所有這些問題不僅沒有緩解,反而變得嚴重了。這裏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如果這些不能得到有效的改革,那麼通往諾獎的道路依然會是很遙遠的。
除了這些研究者們所面臨的環境,另外一個因素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研究者們成長的土壤。土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都是在這塊土壤中成長起來的,等進入從事科研的階段,人的個性已經成型了,很難再有實質性的變化了。前面所討論的研究者們追求利益的功利主義個性,就是在他們生長的土壤裏面形成的。其實,前面討論了那麼多的體制機制問題,但這些體制機制問題的生存和韌性就和人的個性密切相關,人與體制是互為因果的。
說到土壤,人們不得不指向一個人從小到大所經歷的教育體系。
在所有文明中,再沒有其他文明像中國文明那樣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了。數千年被接受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家所提倡的「有教無類」理念有幾層意義:第一,所有人是可教的;第二,教育不應當分階層和階級,人人在教育面前平等;第三,所有人可以通過教育從「野蠻」轉化成「文明」。直到今天,這些教育價值無疑依然充滿着現代性。
問題在於,為什麼如此強調平等的教育價值觀沒有導向人們所希望的人才培養?

這裏的原因很複雜,但如果從哲學層面說,主要是人們沒有搞清楚「人」與「才」的關係。人們經常說人才,但人才的基礎是「人」。中國傳統也一直在強調,先做人,後做事。但經過我們的教育體系的培養,正常的人不見了,各方面的「才」則層出不窮,並且這些不同類型的「才」在利益層面實現了完全的統一。經驗地看,很多人也在抱怨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我們的學生過於功利主義,做什麼都有太明確的目標,都是為了自己的「小算盤」。
在很大程度上說,迄今的教育秩序的終極目標不是培養「人」,而是培養「才」。跳過了培養「人」的階段而直接奔向「才」的階段。更為嚴重的是,這個「才」不是學生自己決定和選擇的,而是家長、幼兒園老師、小學老師、中學班主任、大學教授等等決定的。這些也就是前文所說的廣義上的「組織」,在這些「組織」裏面,人便是工具而已。
中國的學生並沒有太多機會來尋找自己的興趣——真正屬於自己的興趣。中國的家長大都是「望子成龍」型的,總是對孩子抱有過高的期望,並且要透過施加壓力的方式在孩子身上實現自己的抱負。中國的老師,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是以自己的「興趣」(或者說是社會賦予其身上的責任)來塑造學生的。
進入現代社會,教育系統更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有效工具,也就是說,學生也必須實現國家的「興趣」。對各個層面的權力載體(無論是政治還是資本)來說,培養人才就跟生產「土豆」一樣。人們所抱怨的包括應試教育在內的種種現象便是這個過程的必然結果。
到了今天,這種局面已經到了不得不加以改變的時候了,因為這種局面的延續對學生、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都是不利的,更不用說要實現人們摘得諾獎的目標了。
這就需要人們重新思考中國教育體系的重構問題,就諾獎來說,也就是解決培養土壤的問題。
〈中國的諾貝爾獎「躁動」〉二之二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