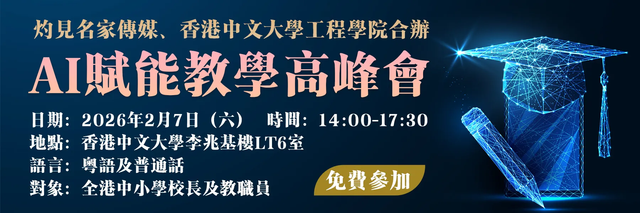美國總統特朗普於7月4日簽署《大而美》法案(OBBB),世界輿論一片嘩然。人們普遍認為,《大而美》法案本質上是一次以減稅為核心、以壓縮社會保障支出為配套的財政重構工程,因此展現出高度結構化的「逆向再分配」特徵。
的確,很多數據都指向這個方向。法案將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的多數條款永久化,未來10年減稅規模高達4.5兆美元,其中企業與高所得群體獲益最大。同時,約1.7兆美元的財政缺口將透過削減底層民眾依賴的福利項目填補:包括對醫療補助(Medicaid)和食品援助(SNAP)實施新的工作門檻、設立聯合支付機制、推動各州分擔SNAP誤差成本等,預計將有1180萬人失去醫療保險,另有300萬人失去食品援助。
法案對老年人、身心障礙者和低收入家庭的制度性支持空間被顯著壓縮,但對高淨值人士和資本所得減稅條款得以延續乃至擴大。根據耶魯大學政策研究中心估算,未來10年,美國收入最低20%人群的年均稅後收入將下降2.9%,而最富裕20%人群將上升2.2%,貧富分化在稅制層面被制度性固化。再者,大學捐贈基金課稅上調、匯款附加稅、清潔能源補貼取消等條款,都將影響教育、環保與移民群體的可近性與權利保障。
因此,整體上看,該法案以犧牲基礎公平為代價強化選民經濟,重塑美國社會分配格局,其政治本質是對「新自由主義──福利國家」模型的系統拆解。
如果從這些角度看,這個法案無疑是倒退的,甚至是落後的和反動的。一些批評者更是無中生有地認為,這部法案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而是「讓中國再次偉大」。(當然,在中國,也有人認為,這是針對中國的法案!)

法案的政治本質:美國保衛戰
不過,一位朋友剛從美國考察回來。他拜訪了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多所大學,並與當地的教授們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他被多次告知,特朗普所進行的是一場美國保衛戰。儘管這場美國保衛戰很難如特朗普所願那樣持續下去,但的確是「特朗普(們)」保衛美國的最後一次機會。
這一觀點儘管沒有在西方流行起來,但較之任何其他觀點都更為深刻,直指「大而美」法案的本質。也就是說,討論《大而美》法案不只是看法案本身的條文,更需要理解其背後的議程,即美國保衛戰。
傳統美國定義與變遷
說這是美國保衛戰,那麼問題在於保衛什麼樣的美國?這裏的美國由誰來定義呢?特朗普是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產物。他的第一次當選普遍被視為美國白人(即MAGA運動的支持者)的公投。那麼,人們不妨從這些白人的角度來定義他們所認知的美國。
今天人們所見到的美國由17世紀從英國出發的清教徒定居者所創立。此後,不同國家的移民來到美國,但當他們來到時,美國已經形成了盎格魯-新教文化。21世紀前美國的移民一直不佔主流:從1820年到2000年,外國出生者平均僅略高於全國人口的10%。

因此,美國的文化主體是盎格魯-新教文化,其主體要素包括:英語、基督教、英式法治理念、司法、限制政府權力的傳統和個人權利理念;新教的價值觀,包括個人主義,工作道德;源自歐洲的文學、藝術、哲學和音樂傳統。
正是因為美國是個移民社會,而且大都是反抗舊制度或對舊制度不滿的移民,因此,美國人形成了特有的所謂的美國信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兼有自由和平等的個人主義、人權、法治和私有財產制等。與母國文化相比,美國清教徒的持異議色彩帶給了美國信念的更加「強烈自由精神。」
在過去,人們常用「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縮寫),也就是「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來形容美國。《劍橋字典》將此解釋為「祖先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白種人,也被認為是美國社會中勢力最強大、最富有的白人」。
這個概念最初(1957年)由政治學家安德魯・哈克(Andrew Hacker)所使用,但當時的「W」代表「Wealthy(富有)」而非「White(白人)」,後來的人們則以「W」來指稱白人。不過,這字之改,使得這個詞更直接指向了這個群體的種族本質。德國社會學家 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是在信奉新教倫理的人口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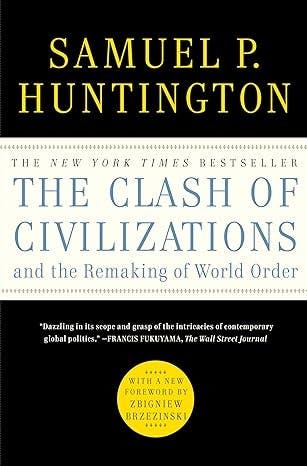
(Amazon 書影)
亨廷頓理論視野下的美國文化衝突與國家認同挑戰
但是,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美國已經不是原來的美國,所有這些傳統特徵都不再能夠定義美國。不僅如此,這些特徵的流失被視為已經威脅到人們傳統所認知的美國的存在了。
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人相信美國是一個大熔爐,文化多元主義盛極一時。儘管對多元文化論題的討論不時在美國發生,不斷有人提出質疑,但左派沿着這個思路不斷發展,形成了今天特朗普陣營所竭力反對的「多元化、公平與包容」(The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DEI)。
不過,更早的時候,對這個問題的系統論述和質疑的是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93年,時任哈佛大學教授的亨廷頓在雜誌《外交事務》上發表了題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衝突?〉的文章,即刻在美國內外引發巨大而持續的討論。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為在蘇聯解體之後,伊斯蘭必將成為西方主導的世界的最大阻力,因此,西方的下一次大戰對象必然是伊斯蘭世界。
1996年,在此基礎上擴展,亨廷頓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一書。 在這本書中,亨廷頓再次強調,蘇聯解體之後,冷戰期間資本主義的西方集團和共產主義的東方集團之間的衝突會被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取代。
亨廷頓界定了9個主要的文明,包括西方、拉丁、伊斯蘭、中華、印度、東正教、日本、非洲、佛教。他認為,要理解當前和未來的衝突,就必須理解文化衝突,文化(culture)──而非國家(the State)──成為戰爭的理由;如果西方不承認文化緊張的不可調和性質,那麼西方就不可避免地失去其主導地位。因此,亨廷頓建議,西方必須從文化上強化和鞏固自身,而放棄民主普世主義和對他國的軍事干預。
在很大程度上說,亨廷頓的著述是對其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名噪一時的歷史終結論的回應。在歷史終結論中,福山認為蘇聯集團解體之後,西方民主就可以終結歷史了,即認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是人類歷史所能擁有的最好也是最後的政體。現在看來,亨廷頓是對的,而福山則是錯的。

亨廷頓並沒有就此為止。2004年,他出版了生前最後一本著作,即《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將文明衝突觀由國際轉向美國國內,論述了美國國家認同所受到的種種挑戰,並把此提高到國家安全的層面。
杭廷頓明確指出,美國認同正在快速減弱。從歷史上看,美國的認同涉及四個主要組成部分:人種、民族屬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語言和宗教),以及意識形態。或者說,對一個國家的認同(即所謂國家凝聚力)一般由種族、民族、領土、文化和意識形態所組成。
但是,在美國,對國土自豪的人僅有5%,對政治體制最引以自豪的美國人有85%。可見,對美國人來說,意識形態重於疆域。人種和民族單一的美國不復存在;美國的文化受到解構主義的攻擊;美國認同只剩下意識形態。但蘇聯的解體表明,在缺乏人種、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況下,意識形態的黏合力是弱的。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是永恆的。正如盧梭所言,「既然斯巴達和羅馬都滅亡了,還有什麼國家能希望永世長存呢?」即使是最成功的社會,也會在某個時候遇到內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脅,或者受到更加激烈和無情的外部野蠻勢力的威脅。在亨廷頓看來,美國最終也會遭受斯巴達、羅馬等國的命運。
亨廷頓進而認為,儘管美國社會的生存受到嚴重挑戰,但透過重新振作國民認同意識,振奮國家的目標感以及國民共有的文化價值觀,能夠推遲其衰亡,遏制其解體。
概括而言,亨廷頓要表達的意思是:如果說在冷戰期間,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外部的蘇聯集團,那麼在後冷戰時代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則主要來自美國內部。
如果從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來理解MAGA運動和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是否可以看到其更為深一層次的意義呢?
前途未卜的特朗普美國保衛戰 二之一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