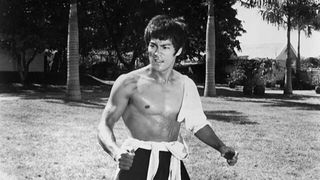武俠小說內的英雄豪傑,都是行俠仗義,保家衞國,決意要把一身武功鍛鍊至有高山深海般的力量的;但現實中,要達至富國強民,實不能單以武力為尚,一味窮兵黷武反而與平和安穩背道而馳。金庸以「黃藥師」之名代入梁啟超的事蹟來編寫《射鵰英雄傳》,已是在暗示,欲達致國家強盛、民智大開之願景,必須要運用任公所開之藥方:育民施教,開啟民智。
梁啟超從公車上書到戊戌變法期間,已為中國教育的變革而奔走。他並非只是夸夸其談地評論政事,他執掌「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遊說清廷廢除科舉(按:後來倡復),參與籌辦北京大學之前身京師大學堂,更倡興女學 ——其夫人李蕙仙也有參與籌備中國首間女子學堂。任公肩負各樣的重責,為之鞠躬盡瘁,終於積勞成疾。
至於家教,讀過梁氏溢滿父慈子孝的家書便得知,任公不分男女一視同仁,同時他從不強迫子女順從己意,只會誘導他們跟隨各自的意願選修學系。徽因痛失父親後嫁入梁家,任公視如己出,悉心栽培。可見任公於百多年前已親自體現了超越時代的教學理念。
論到革新文學,在晚清到民初之間的「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革命」以及「戲曲革命」當中,任公都是名符其實的開拓者與力行者,這些顯赫功勳就足以奠定他應有之歷史地位了。
本文會分開幾部分,為讀者簡介梁啟超對查良鏞的教育事業以及創作小說的影響;另外會列舉幾段梁查二人可能是巧合的,又或者可能是查良鏞有意無意間,走過和任公相似的人生軌跡。
退隱江湖,作育英才
金庸武俠小說裏面的英雄俠客,在飽經滄桑看透世情之後,多會遠離江湖避世隱居。梁啟超於1920年歐遊回國後,對政壇爭鬥意興闌珊,毅然遠離是非,專研學術;五年後他重執教鞭,被譽為清華四大導師之一。
機緣巧合下,查良鏞亦走上近似的命途;辭任《基本法》草委,卸下《明報》筆政後,他亦置身於教育事業。1994年浙江大學邀請金庸出任文學院長,後來本身已獲頒名譽博士授銜的查良鏞,仍不休不倦地回到學堂求學,一償以實學成績成為博士的宿願。
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與「降龍十八掌」
細看金庸筆下的黃藥師: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柴米油鹽、醫卜星相樣樣精通;門下徒生俱是允武允文,尊崇師道;此之謂一代武學宗師,非逞勇之莽夫可比。筆者早已認為金庸着力塑造一位文武雙全的嚴師。金庸如何把任公對教育的心法寫入作品呢?其實也不難找到答案,我們可以從任公生涯中,幾段與教學相關的事蹟,以之對比《射鵰》的情節和場景,自然能透解箇中關係。
1914年在清華學校一場主題為「論君子」的演講,任公闡釋《易經》乾坤兩個象辭——「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的精髓,以勉勵學子不屈不撓,奮發圖強,興家為國,作國家的中流砥柱的精神,同時又當胸襟廣闊,有容人之量。兩句象辭隨後被校方採納成為校訓,兩岸的清華大學皆沿用至今。
讀者可曾想過,金庸為何以《易經》象辭為「降龍十八掌」各路招式定名呢?當啞謎破解後,一切都變得簡單易明了。如同把「打狗棒」和「軟蝟甲」替換配對,金庸又故意「調轉」乾坤;挪移梁任公提出的易經象辭,編成由丐幫洪七公始創,獨步天下的武功招式。
反觀現實,任公兒子思成就學於清華,後來擔任清華大學教授;所以金庸也定必要郭靖師從七公,並修練這套蘊含《易經》智慧的「降龍十八掌」。既然是從任公的演講取得靈感,黃藥師生平最佩服這套武功也是理所當然了。
原來如此!筆者呼籲清華的師長學生們,今後請謹記大學校訓所隱藏的這套絕世武功的要義,並深入領悟第一式「亢龍有悔,盈不可久」的心法與任公演講內容共鳴共通之處。明瞭當中的道理之後,大家就會如醍醐灌頂,悟出一套能夠終生受用的好武功。另外要略略一提第十八式「震驚百里」,金庸藉此透露《武穆遺書》是代表蔣百里的著作《國防論》。
這個發現又再證明金庸就是黃蓉,《射鵰》書中一事一物亦須以「調轉」去詮釋理解。折服天下,威力無窮的「降龍十八掌」原來是文質彬彬、謙謙君子的修身訓言。表面是南轅北轍,可是細味任公所引象辭,又會感覺當中深藏着堅貞不二的浩蕩俠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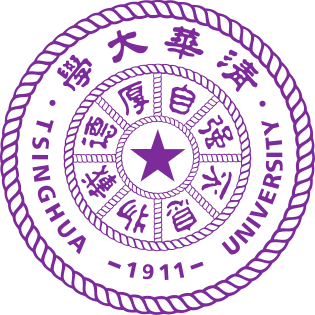
穿越百年聽任公演講
知道金庸創作「降龍十八掌」的原由之後,讓筆者再和大家穿越時空回到1922年,上任公主持的課堂。簡單來說,我們只要一讀雅舍主人梁實秋先生一篇著名散文《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注),就可以仿如親歷其中,目睹任公的風采。這個座無虛席的演講主題是《中國韻文裏表現的情感》。梁實秋先生描述任公用帶廣東口音的官話作開場白,當中兩句「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已讓人有「任公躍然紙上」的感覺。文中又提到,任公呼喚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當講到任公極其讚賞的清初戲劇《桃花扇》中「哭主」一齣哀慟人心的情節,任公悲從中來,竟然當堂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甚至要掏出手巾來拭淚。再講到任公認為是「情聖杜甫」的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時,任公又會在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任公在課堂上的攝人風範令梁實秋多年以後都難以忘懷,他認為任公是有學問、有文采、有熱心腸的學者,也驅使他踏進中國文學之路。
在演講授學方面,查良鏞可謂不遑多讓。他常自謙學識淺薄,難以為師,對後輩學生以大師兄自居。但每次有大學舉辦金庸演講會,必然引得師生爭相捧場,造成萬人空巷的境況。相信他當時也會滿心歡喜,因為自己那一股瘋魔學界的魅力,大概也能與任公媲美矣。
言歸正傳,筆者從這場演講內容發現兩則與《射鵰》謎團有關的重要線索。首先,任公極之推崇劇作《桃花扇》,即又再多一則有力證據可證明桃花島主人就是梁啟超。而另一重要線索,是任公喜歡杜工部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末一句提到襄陽;「……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也就是郭靖黃蓉要守護該城之一大主因。
筆者已可肯定金庸也有讀過梁實秋先生這篇散文,並從而獲得創作《射鵰》故事情節的靈感。而在筆者記憶中,最初認識梁啟超先生,是在課堂讀過他的大作《敬業與樂業》這篇範文;文中的意義筆者至今仍牢牢記得。最後,也一如書中郭嘯天和楊鐵心,筆者也慨嘆遲生了一百二十年,否則便有機會上一堂任公主持的課堂。
梁實秋是梁思成在清華的同學,同年的還有聞一多和孫立人等。下一部分筆者會為大家介紹《射鵰英雄傳》內任公的三位入室弟子。
(注)梁實秋這篇《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也已成為中港台三地的教學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