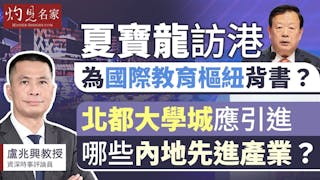耶魯大學英國文學批評家朗斯伯萊(Thomas Lounsbury,1838—1915)在其《戲劇藝術家之莎士比亞》中,一語道出近代以來對莎氏悲劇《馬克白》(Macbeth,約1606)黑暗心理的詮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罪惡一旦掌握了一個人的靈魂,其逐漸使人變質的力量是如何偉大。這種力量在不同的性格上產生出不同的悲慘效果,對於此種效果加以研究是非常饒有心理的與戲劇的意味的。」(註1)鄧樹榮應英國莎士比亞環球劇場(2015年8月)與第44屆香港藝術節(2016年3月)聯合邀約執導《馬克白》,雖然承認莎翁是「高超的『心理學家』」,卻把開幕登場的三個「女巫塑造成實在的角色,而不只是馬克白內心的魔鬼」,讓穿着現代服裝(譚嘉儀設計)的馬克白「夫妻自夢中醒來……開始思考在現實的昏亂世局中自身所處的位置」(註2)。於是,為這齣莎劇的現代、現實意義套上了夢的框架。當年弗洛伊德以莎氏另一部悲劇《哈姆雷特》大膽論證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意結,面對《馬克白》卻只能解釋主角二人因無子嗣,為保弒君得來的權位不致旁落而大開殺戒。(註3)設若弗氏100年後看到鄧氏的《馬克白》,又將如何釋夢?

儘管賦予莎劇現代色彩是當今演繹經典的慣用手法,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製作不乏其例,然而劇評人洛克斯頓(Howard Loxton)在倫敦觀看粵語版《馬克白》後仍不明白有什麼需要加上夢的層次。(註4)究其原因是鄧樹榮的簡約美學(minimalist aesthetics):一對現代男女「穿越」中國古代,進入《馬克白》的劇情,歷經殺戮,最後夢醒,舉傘,跳下舞台,劇終。所謂「現實的昏亂世局」只是導演接受環球劇場訪問及其他媒體報道時的談話內容,(註5)既沒有像鄧導演的另一齣莎劇《泰特斯2.0》那樣在開場前廣播國際及本地新聞,也沒有用早晨城市甦醒的雜聲作音響效果,就連馬克白夫人讀的信亦沒有現代化成電腦或手機,陳鈞潤和導演本人中譯的台詞更不沾潮語;只有靜默的佇立、凝鍊的動作、幾套現代服和劇終的黑傘,並無其他現實的具體指涉。如此乾淨的零度提示,不着一字,任憑觀眾各自浮想。難怪《演藝風流》節目主持盧偉力從馬克白扯到毛澤東,洛楓則由黑傘聯繫上雨傘運動。(註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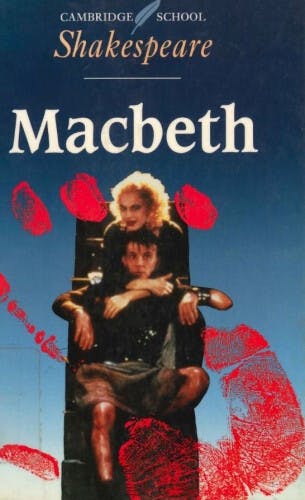
持續鬥爭的夢魘
文藝心理學家萊沙(Simon O. Lesser)在〈馬克白:戲與夢〉中認為馬克白殺人乃出於其自我(ego)意識無法逃出超我(superego)道德與本我(id)衝動之間持續鬥爭的夢魘。(註7)野心勃勃卻軟弱無能的馬克白做了場短暫的帝王夢,死於復仇的劍下;而使他雄心勃起的狠毒夫人則由夢遊陷入瘋狂,終於自縊。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兩人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人格分裂(因此馬克白有「女性」不忍的一面,而馬夫人則有「男性」殘忍的一面),在本我的欲望實現後,自我反而永無寧日。(註8)誠然,正如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邱錦榮指出的:「弗洛伊德的精神探求在於莎劇的內容和人物甚於其詩意、形式或風格。」(註9)而鄧樹榮則善於把這種內心掙扎的戲劇張力通過演員的形體表現,表演出來。韋羅莎把馬克白夫人的情緒變化呈現得絲絲入扣,尤其是對夫君肆意慫恿、操控──那個騎在他背上的動作,雙臂像蟒蛇般緊纏着他,雙手鉗住他的頭顱,比前此西方類似的形體設計更顯瘋癲,簡直要把這員蘇格蘭大將整個吞噬!而當馬克白幻見捉摸不定的殺人匕首,導演讓黑衣人在主角眼前揮舞亮劍,燈光幽暗卻沒完全熄滅,觀眾依稀可見舞劍者扭動着身體游刃空中。(註10)不在全然漆黑中使用熒光匕首製造更虛幻的視覺效果,正是要請觀眾欣賞演員的肢體表演──有如觀看京劇折子戲〈三岔口〉──產生劇場的疏離感,與夢境保持距離。

其實,鄧樹榮讓配角都穿上中國古代服飾,並非要像黑澤明的經典電影《蜘蛛巢城》(1957)那樣把這齣欲望悲劇整個改編過來,(註11)而是為了方便展現東方的形體美學。因此,人名、地名不妨依舊是英國的,慢動作武打卻是中國的,舞踏的風格又是日本的──反正夢的邏輯可以自由飛越古今中外。劇中加插鄧肯駕崩後鬼魂登場,面上的京劇臉譜化妝更是神來之筆,可惜現身時間太短,觀眾無暇細賞。(註12)至於梁暐嶽現場演奏的韓國鼓,緊湊悠揚,亦不下於土取利行(Toshi Tsuchitori)同時在香港藝術節演出彼得·布祿克(Peter Brook)《戰場》(Battlefield)中的鼓樂。其結果是糅雜了今日香港、古典中國、日本舞蹈、韓國音樂等多種東亞元素的英國劇。這就是後殖民時代劇場內外混雜的香港身分嗎?而這場曖昧不明、模糊不清的香港夢,在緩慢的、沒有短兵相接的刀光劍影之間(每次刺殺、交鋒均保持距離),又如何觸動了英國前殖民者、倫敦華人、本土及內地觀眾,以至英、港兩地中外遊客的心靈?(註13)
(下篇討論上月中旬第10屆華文戲劇節鄭傳軍導演的《馬克白》。)
註1:Thomas R. Lounsbury, Shakespeare As a Dramatic Artist: With an Account of His Reputation at Various Period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8), 415: “It is the gradual transforming power of sin, when once it has taken full possession of the soul, which here arrests the attention. It i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 of the devastation wrought by it in different natures which furnishes a study as full of psychological interest as it is of dramatic.” 梁實秋譯:《馬克白》,《莎士比亞全集》第31冊([臺北] : 遠東圖書, 1968-76),8。
註2:鄧樹榮:〈導演的話〉、〈鄧樹榮談改編莎士比亞的《馬克白》〉(李凱琪譯),載鄧樹榮戲劇工作室:《馬克白》場刊(香港:香港藝術節協會,2016),14、16;粗體為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