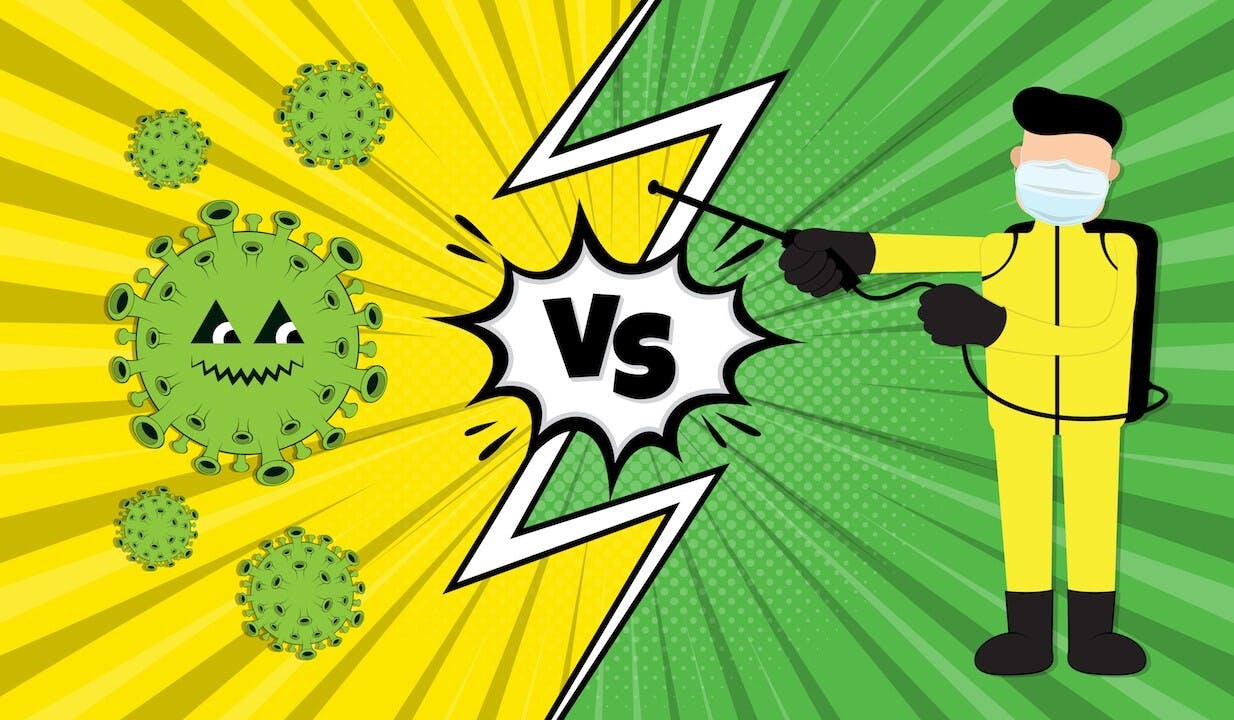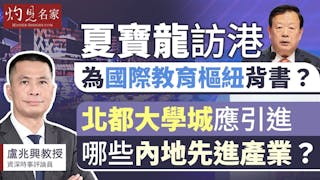2019冠狀病毒的起源和擴散,指向了人與自然關係中的嚴峻問題。儘管人們對病毒到底源自哪個國家並無定論,科學界公認病毒源自人與自然的不當接觸或互動。這就要求人們必須也應當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因為如果人類找不到一種與自然相處的合適關係,不同類型的病毒會不斷重現,影響甚至懲罰人類。
病毒本來就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一部人類歷史也是一部病毒產生和傳播的歷史,一部人類和病毒較量對抗的歷史。人們可以自信地預測,這部歷史永遠不會終結,所不能預測的只是病毒和人類兩者之間誰主沉浮的問題。
病毒的存在是客觀的事實,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病毒和人類建立關係則是人類文化活動所引起的。早期,隨着農業的發展,人類的足跡開始到達偏遠的五湖四海。近代工業化和城市化更是完全消滅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邊界,史無前例的道路建設、森林砍伐、土地清理,使得野生動物居無定所,人類就是這樣在自身和野生動物之間確立了緊密的關係。伊波拉病毒、沙士(SARS)、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以及現在的冠病病毒,都與野生動物有關。大範圍流行病通常始於動物體內的病毒,當人類與它們接觸時,病毒就到人類身上。
人類在野生動物上所發現的商業利益(利潤),更是促成了野生動物貿易進入城市中心,搬上了人們的餐桌。寵物業的迅猛發展,使得愈來愈多的野生動物甚至變成了很多家庭的核心成員。在香港,人們發現寵物狗也感染了冠病病毒。發現動物感染病毒並非什麼不尋常的事情,此前沙士和中東呼吸綜合徵都有類似的案例發生。因為人類的自私性,寵物在很多場合變成了棄物,如果寵物也可以傳播病毒,那又會增加病毒擴散的途徑。
病毒的全球化
隨着近代開始的全球化而日趨增長的旅遊和貿易等活動,也促成了病毒的全球化。冠病病毒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已經導致愈來愈多人對全球化做深刻的哲學思考。病毒不僅對本來已經放緩的全球經濟造成了又一次的沉重打擊,而且促使人們從更深層次對全球化的觀念發生了質疑。在圍繞世界該怎樣整合或分離的激烈辯論中,冠狀病毒的傳播可能是一個決定性時刻。甚至有人認為,冠狀病毒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是對全球化的最後一擊,或者是壓在全球化駱駝背上的稻草。
對科學的迷信更是人類對病毒傲慢態度的來源。近代以來的發展無疑是人類科學技術進步所推動的,這導致了愈來愈多的人深信科學是萬能的,總是有能力制服任何一種病毒。從政治人物到普通民眾,人們似乎都把病毒當作自然災難來應對,坐等它們發生,並天真地相信一種新病毒發生後,人類能夠迅速研製出疫苗或藥物。
不過,事實遠非如此。直到今天,人類仍然沒有能夠研發出針對2002年、2003年沙士病毒的疫苗,也沒有針對愛滋病、寨卡病毒(Zika)或一系列新出現的病原體的疫苗。實際上,人類的利己性質往往給病毒和病毒的變種很多機會和空間。經驗表明,在兩次疫情暴發間隙,各國(無論是怎樣的政治制度)行為表明,因為政府的短視和資本的趨利性質,造成了投入資金預防的意願大幅度減弱,針對零星病毒性疾病的疫苗和藥物市場,不足以推動研究和開發。
也就是說,人類在病毒面前往往表現為無奈。如果這樣,人們就要重新思考和定位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在人類和自然的關係上,無論東西方,人們的認知是有一個過程的,但總體上看,這是一個人類從謙卑到狂妄的過程。
在西方,這種變化表現在自由主義的演變過程之中。在東方,自由主義更多地是被理解為一種政治經濟思潮。不過,西方自由主義也表現為一種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近代以前,在亞里士多德式對自然的解釋中,人被視為是自然秩序的一個內在部分;人本身被視為是被自然固定的終極點,是不可改變的。
既然人性與自然世界秩序具有一致性,人既要和自己的本性保持一致,也要和自然世界保持一致。儘管個人的確可以自由地與自己的本性和自然秩序背道而馳,但這種行為會損害自己,既破壞人類的善的方面,也破壞自然秩序。在中世紀,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神學還是阿奎納神學,都試圖闡述自然給人所設置的限度。
近代以來的自由主義哲學,則拒絕所有這些自然加於人類之上的限制。就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自由主義經歷了兩波革命。第一波革命發生在文藝復興,主張人類應當應用自然科學和經濟的力量,去實現對自然的主導權,成為自然的主人。就思想淵源來說,第一波革命始於英國的培根。
培根質疑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主義的自然觀,相信並主張人類對自然的主導和控制權。培根的這些思想是西方早期自由主義的基礎。自由主義驚訝於自己對經濟秩序的大發現。他們發現,基於自由市場基礎之上的經濟制度,可以為人類所用,是人類征服和主導自然的有效武器。
不過,早期自由主義還是認為人性是固定的,不可改變的。或者說,就其本質來說,人性是惡的,人性的惡可以被各種因素所遏制,但惡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因此,早期自由主義者一方面認為,人的惡可以用來增進經濟和科學制度,從而增進人的自由,提高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認為人類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例如分權制衡)來遏制惡,使得惡維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程度。
第二波革命發生在19世紀,這波革命徹底改變了自由主義者對人本身的看法,認為人的本性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有能力改變以求得道德上的無限進步。自由主義者把第一波革命稱為保守的自由主義,而把第二波革命視為是進步的自由主義。
第二波革命的自由主義者對第一波自由主義的人與自然觀都持批評態度,認為他們都不夠進步。不難發現,從盧梭到馬克思,從密爾到杜威,到當代各種跨越人類主義者(transhumanists),人們都拒絕人性是固定不變的觀念。他們想把第一波思想家的人類征服自然的想法,應用到人類征服人性本身。今天的跨越人類主義者認為,人類可以借助科技促成人類本身超越其物質和心智的限度而得到演化。生物基因技術的發展正在使得愈來愈多人相信,死亡基因終將被發現、被剪除,人可以超越年齡的自然限制而得到永生。
天人合一與人定勝天
在中國,人們對人與自然的看法也基本上經歷了類似西方的進程,也是一個從謙卑走向狂妄的過程。中國古代哲學家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把人類看作自然界的一個和諧的組成部分。天人合一的思想影響了中國古人對其他各種社會關係的看法,可說是很多思想的源頭。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因此認為,天人合一思想是整個中國古代思想體系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上面提到的西方亞里士多德和阿奎納等人與自然一致性的思想,並沒有多少差別。
當然,天人合一並非主客不分。主客不分的觀念在《莊子》那裏是存在的,但只存在於哲學層面,在實踐中則行不通,因為在現實中,人還是人,山還是山,儘管兩者是一體的。正因為人與自然實際上是分開的,如同西方,中國古人也提出了人定勝天的進步思想。《逸周書·文傳》稱人強勝天。宋·劉過《襄陽歌》稱,「人定兮勝天,半壁久無胡日月」。清·蒲松齡《聊齋志異·蕭七》稱,「彼雖不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
這些表述儘管有些不同,但總體思想是一致的,即人具有主觀能動性,能夠發現自然運行的規律,根據規律和自然打交道。無論是大禹治水的傳說,還是戰國時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例子。這也表現在軍事戰略上,例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說法。天時可理解為機遇或氣候條件,地利為有利的地理條件。天時地利都是軍事較量中取勝的重要因素,比如諸葛亮借東風,周瑜火燒赤壁,打敗曹操百萬大軍。
近代以來,人定勝天的含義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西方的各種主義流入中國,任何一種主義都往往以最為激進的形式出現;同時,在各種主義競爭過程中,那些溫和的最終都被淘汰,生存下來的都是激進的。這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因為傳統中國被西方列強所打敗,要求民族和國家的生存,就必須採用甚至較之西方更為激進和極端的方式。
在這個過程中,傳統上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人定勝天被推向了極端,演變成人戰勝自然,主導和控制自然。所謂的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便體現了這種極端思想的趨勢;甚至很顯然,這裏的人(他人)也變成了自然(客體)的一部分,是個人必須鬥爭和征服的對象。
在和自然鬥爭方面,如果說西方發現了市場自然秩序,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則發現了基於權力之上的政治自然秩序。不同的發現有其歷史的根源,因為發展中國家如果僅僅依靠市場秩序,就不足以和西方競爭,更不用說戰勝西方了。所以很多國家就轉向政治,通過政治來塑造強大的國家秩序,打敗西方。以政治組織的力量來征服自然,這就成了很多國家的信仰和實踐。久而久之,人們開始視這種基於權力之上的政治秩序為自然秩序,即不是一種人為製造的制度,而是一種超越人類的制度。
在中國,人定勝天似乎表現得更為極端。這裏有被視為失敗的例子,例如大躍進(與自然鬥爭)和文化大革命(與人鬥爭)等,也有被視為非常成功的例子,例如三峽大壩和舉國體制等。不過,人們似乎對過去的失敗沒有記憶,而只在意成功的榮耀。
記得在本世紀初(2005年),中國一家官媒採訪了一位很有名氣的科學家,採訪稿就以〈人類無須敬畏大自然〉為標題而公開發表,以最直接和坦白的方式表達了人類對自然的鄙視。儘管這種傲慢的態度,近年來因為治理環境的需要而有所節制,但人們對舉國體制的崇拜則不僅沒有減弱,反而變本加厲。
無論中西方,人類因為經常遇到像冠病病毒突然暴發那樣的事件,而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更不用說其他像地震、海嘯、氣候巨變等自然災難了。光是病毒,科學家估計,人類生活的世界裏存在167萬種未知病毒。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和自然的鬥爭會一直進行下去,即努力發現這些病毒並進行測序,並在此基礎之上發現疫苗和藥物。不過,就本質來說,這與其說是和自然的鬥爭,倒不如說是人與自己的鬥爭,因為病毒本身就是人與自然不恰當的互動方式而出現的。
如果說人定勝天意味着人類利用理性認識自然規律,根據自然規律和自然相處,人類就會向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境界靠近一步;但如果人定勝天意味着人類以狂妄自大的方式去征服自然、做自然的主人,去征服人類本身做他人的主人,這不僅駕馭和控制不了自然和人類,反而最終會把人類導向一個恐怖的X時代。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