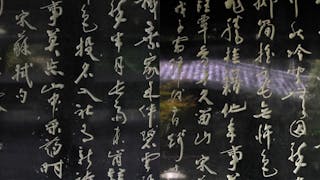執着猶如手中緊抓的一個東西,以為放下就是要刻意讓東西掉落遠離自己,殊不知真正的放下,只要把手心向上打開,東西不再受束縛,卻也不一定要掉落。

透過學員和嘉賓們雙手與心靈的協作,讓泥土化成了獨一無二的陶藝作品,我們為此辦了一個「土中覺 茶中禪」展覽。希望大家在觀賞之間,能夠靜靜覺察身體與呼吸。

生活中雖不能控制其他人、事、物的發生,但卻可以決定自己對人、事、物的態度。

除非要考查研究歷史,否則我們不需要刻意花時間去考證典故的真偽,重要的是這個典故對我們有何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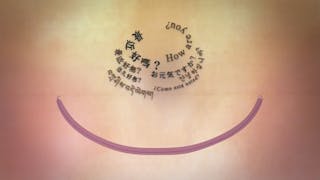
透過禪修學習自我覺察的能力之後,對於分辨吸收資訊的好壞能力也會大幅提升,大家是否要坐言起行,立即開始持續練習呢?

近年一直推行的「停一停 心呼吸」,其實就是禪修之中「止」和「觀」的理念,「停一停」就是「止」,「心呼吸」就是「觀」。

我們的心是最珍貴的房子,最值得愛護。內心只值得放美麗的風景,放最美好、最有價值的事情。

只有平靜下來,內心澄清了,事情也變得清晰,才能找到解決的方法。靜坐和禪修能讓我們的心清晰明淨,培養出更高的覺察力和集中力,用自己內在的力量,轉煩惱變為智慧。

千萬不要花無謂的時間,去刻意分別計較自己現時的修行是在哪一個境界。

學佛禪修其實是一件簡單但卻不太容易的事,以前自己都是千方百計想要找到方法,近年才發覺只要老老實實修行便好了,重點始終是要去做,才能真正體驗得到它的大益處。

人生尋尋覓覓,紅塵紛擾,一切痛苦煩惱,皆自心自造。世事茫茫。願你我能放下執念,不為情牽,不為物累。

試着每天留出幾分鐘,靜靜地與自己相處。或許,你會發現,真正的佛法並不在經書中,而在你的心裏。

人人皆有佛性,本自具足,因此不論身處在貧或富、簡單或複雜的環境中,都能得到自在的生活,只是我們尚未證悟,因迷失而經常做出錯誤的決定。

心理健康,身體即使有病也比較容易治療;如果心理不健康,身體再怎麼好也是有問題的,對社會、家庭都可能造成困擾,大家千萬不可掉以輕心啊。

「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增;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眾生」, 以我自己的經驗,在敲鐘、擊鼓和唱誦的過程中,身心完全投入,就是一次很好的禪修練習。

清楚覺察心可能會被妄念帶走,但不需要一有妄念生起時,便要立刻消滅或者壓制它,只需要知道它生起了,再輕鬆地返回當時在用的禪修方法,繼續保持覺察,我們的心就能漸漸安住了。

學習將禪修活用,「學」完理論之後,實際的練「習」也非常重要,如果純粹只認識理論而不練習是不行的,但純粹練習而不知道理論,當遇到一些未如所料的情況時,就會無從判斷而不知如何是好,這就是佛法強調的平衡。

為什麼說「人身難得」?因為在六道之中,唯有得到人身才適合修行,以脫離永世輪迴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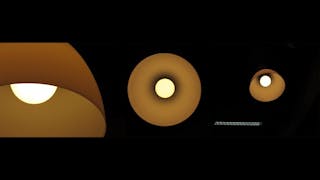
機緣巧合之下,近幾年在懲教署為青少年囚友們舉辦了多次「禪攝影」課程,透過禪修式的攝影活動讓他們覺察當下,從而體會到內心寧靜的感覺,這樣的方式勝過只是講大道理。

佛陀在《金剛經》中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有些人很執着弘法時必須引經據典,否則就不算是佛陀的真正教法,其實就是對佛法太過執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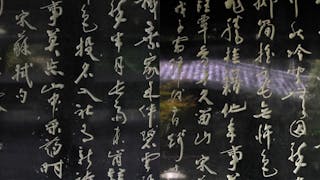
禪宗那套不用語言文字的傳法方式,正正可以跨越人心概念的障礙,更不受任何形式限制,就在日常生活,自然而然,便有可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也就是我們學佛的最大難處,沒有親自體證,是非常難以明白的。

廣東俗語說「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是因為有些事情,不管別人不停告訴你怎麼做的道理,還是不容易做到的,就好像學佛禪修一樣。

腦中不斷生起過去未來、分別計較的這些念頭,都在阻礙我們投入到當下,因此要戒除經常胡思亂想的不良習氣,讓心靈回復原本純淨清明的狀態。

生活中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把心念放在那件事情上面,便不是做表面工夫,而且在過程中還能清楚覺察內外感受,減少東想西想,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如果時刻都能覺知自己在做什麼、說什麼和想什麼,就等於燃點了內心的智慧之燈,每個念頭和情緒都看得清清楚楚,做事便能更加充滿自信,不再被妄念的陰影所籠罩,心內的動力和定力也會同時提高。

很多人只聽從自己腦袋裏的聲音,並且認為是真實不虛,完全交由個人業力的好壞去做主導,曾否想過是被自己的思想欺騙了?

屈指一算,我們在一念之間就製造了81000個生滅妄想,都是圍繞着「貪、嗔、癡」等等煩惱妄想,對我們不但毫無幫助,還會帶來無窮的困擾。

從新聞上看到,很多人覺得隔離是一件苦事,甚至有些人會抓狂逃走,但修行的人卻可以樂在其中,證明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是完全由自己選擇的。

我們會產生恐懼的原因,來自害怕有可能發生的未知,而非必定會發生的事。假如仔細觀察,會發覺恐懼其實只是一種情緒和感受,並不真正存在,只要我們的心經常保持平靜安穩,其實不會那麼容易被它影響。

在生活中,體悟修行。煩惱是培養我們成長的良田,在煩惱中提升自己,才是禪修的真正意義;修行并不是脫離日常生活,而是在人生的點點滴滴之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