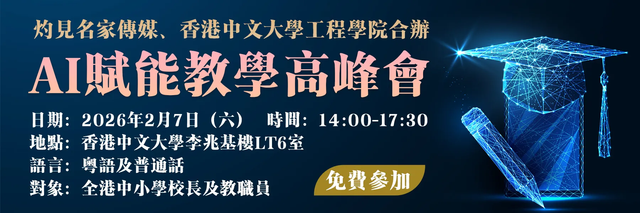常言道:「人靠衣裝,佛靠金裝。」神仙的門面,常常就繫在一襲衣裳上。孫悟空靠金甲與金箍棒,把反叛與自由穿成制服;鍾馗則是另一種活法──他不停換裝,卻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對付不乾不淨的東西。從玄衣朱裳的儺儀群像,到藍衫鬼雄、綠袍進士、紅裳仙官,再到今天數碼遊戲的玄衣戰袍,顏色在換、衣料在換、媒介在換,唯一不換的是角色功能。也因此,他不像某些符號那樣僵化,而是一路在可變的表象與不變的核心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先從最早的「玄衣」說起。《周禮‧夏官》裏的方相氏,領着百二十侲子,「黃金四目,玄衣朱裳」,熊羆面具、握戈執盾、率眾歲末驅疫──典型的群舞圖:一群同樣的面孔,同樣地專職驅厲,而不是某一位名號赫赫的大神,誰站在前頭並不重要。然而到了晚唐敦煌遺書,《除夕鍾馗驅儺文》已能看到「鍾馗」這個名字,S.2055還續上了熊羆、豹皮、朱砂等老牌儺儀符號;可見,他從群相圖中,漸漸出落成一個可直呼其名的主角──有名字、有故事、有能力,「個人化」於是開了局。
藍衫綠袍到紅裳
接下來登場的,是藍衫鍾馗。晚唐周繇的〈夢舞鍾馗賦〉把他寫成「長髯」「闊臆」、「斜領全開」、「藍衫颯纚」的舞者,動詞密集,步伐如節:顧視、蹁躚、頓趾、虎跳……儺舞的狂態雖被文學調過頻,但功能仍舊是逐疫。
北宋《夢溪筆談》更是直接讓鍾馗進入唐玄宗的夢裏:大鬼戴帽,衣藍裳、袒一臂、着皮靴,抓住小鬼就挖眼吞食,問其人,答曰「武舉不捷」,願為陛下除天下妖孽。藍衫在唐代是並非官吏服色,用來套在落第武生身上,別有意味。夢境敘事的魅力,在於它能把怨魂與忠義放在同一幕劇裏:他既是有恨的鬼雄,也能替帝王出力,把鍾馗從儺儀推進了帝王敘事的中心。藍衫,讓鍾馗第一次真正具備了個人身份,他不再是集體儀式裏的無名舞者,而是有背景、有故事的主角。
然而,若只停留在藍衫鬼王的階段,大概鍾馗也只能出現在夜半夢境或村野傳說裏。元明之際,文人再給了鍾馗一塊踏板:皇帝「賜綠袍」。明《繪圖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鍾馗》把情節補齊:終南進士,應舉不捷,觸殿而死;蒙恩賜綠袍而葬,自誓為君煞小鬼。
何謂綠袍?《唐會要》載曰:「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這個細節的妙處,在於賜綠袍不是授官,而是授「合法」:鍾馗雖仍是落第而死的孤魂,但因蒙綠袍恩典,從邊緣「鬼雄」被重新定位為忠烈「人傑」。這種合法性在民間廣受歡迎,於是,民眾開始把鍾馗像堂而皇之地懸掛在門上。試想如果他只是夢裏吃鬼的藍衫惡客,誰敢把他掛在大門迎新?正因有了綠袍的官方背書,他才能從宮廷敘事走向街頭巷尾,成為年節畫像的常客。
等到明末清初上場,鍾馗又把衣櫃翻了一遍,找出一套最適合賀歲的「紅裳」。雜劇〈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為他配置了完整八件套:韶巾、紅襇、偏帶、紅髮、紅髯、笠子、笏與竹節鞭。這套行頭讓他徹底從孤魂野鬼搖身一變,成了福祿仙官。紅色自帶吉慶濾鏡,正合年畫的胃口;繪畫與小說也趁勢擴充功能:仇英筆下的鍾馗《背子圖》,讓他化身祈子守護者;清代高其佩甚至用朱砂來畫鍾馗,以紅色強調驅疫;《鍾馗全傳》《平鬼傳》《斬鬼傳》等一系列章回小說,更乾脆讓他成了文武全才,左掌善惡薄、右持生死筆……於是,生死判官也好,福祿仙官也罷,一身器物、兩手功能、十足娛樂,出場就有戲。

近當代造型
進入近當代,影視作品延續並重組了這些造型。1996年台灣中視的《天師鍾馗》身為福祿之官,還保留着戲曲的影子,韶冠、紅披風、法扇並用;2012年湖南衛視《鍾馗傳說》則把蟒袍、肩甲、寶劍叠加在一起,更符合電視劇的動作敘事。這些影像一面隨意挪用舞臺八件套,一面順手替換媒介所需的器物:笏適合朝堂,不一定適合鏡頭;鞭利於舞台,不一定利於打鬥。服裝道具在影視媒介之間借位換影,鍾馗卻從不離題──他還是在幹老本行:祛厲與護民,保皇的功能雖漸行漸遠,正義的光卻留下來了。
如今,鍾馗在數碼世界裏再次現身,遊戲科學的《黑神話.鍾馗》讓他重新披上「玄衣」。角色造型中,他頭纏巾帕,紅髮紅鬚怒目張,身著札甲護心鏡;手持法扇,身騎猛虎,麾令群鬼提劍立。此造型既呼應《周禮》所載的玄衣,又融入明代戲曲的紅髮紅鬚,並以現代美學重新整合。
設計者並非生搬硬套,而是把顏色、材質、帽巾、髯髮與法器等元素拆解重組,轉化為「戰場—操作」的語法,呈現出符合遊戲審美的暗黑風格。這種處理重視功能導向:既保有可讀性,又強化戰鬥感,一眼即可辨識其為鍾馗。既是復古,也是再造。
鍾馗之所以能在文化長河中不斷被召喚,關鍵不在於他換過多少種顏色的袍服,而在於每一次換裝都能緊扣當時社會的需要,讓角色重新被詮釋。從祛厲儀式裏的玄衣群像,到帝王夢境中的藍衫鬼雄,再到市井年畫上的紅裳福神,直至遊戲螢幕裏的玄衣戰袍,他的身份不斷被重新定位:或是以凶制凶的鬼雄,或是蒙恩的人傑忠魂,或是福祿兼具的仙官,最後成為數位時代的暗黑守護者。這條脈絡既是歷史條件的投影,也是文化適應力的展現。
外觀雖然更迭,但祛厲與護民的核心功能始終如一。正是這種「外表可變、內核不變」,使他得以從祛厲群像中抽離出來,逐步站穩為一個鮮明的個人形象,並最終成為可以跨越媒介流通的文化IP。玄衣紅髯,如今不再只是古籍裏的舊制,而是數位世界裏的戰袍新姿。當我們在遊戲世界裏與鍾馗並肩作戰時,也延續着那場自古未息的驅厲儀式,只是舞台換成了虛擬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