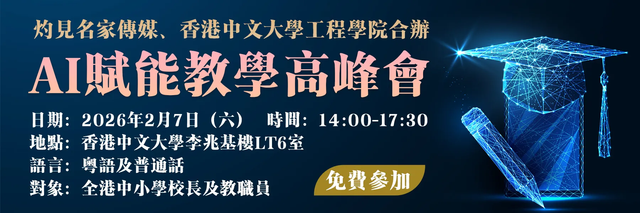實際上,主權國家之間平等的概念產生於西方,也僅僅只適用於西方國家之間。當這一原則擴散到非西方國家的時候,其原則性愈來愈淡薄,甚至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就涉及到國際關係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即國際政治的單元是什麼?是抽象的、沒有差異化的主權國家還是基於文明之上的具體的、差異化的國家?
戰爭與宗教文明
歷史上,文明之間的衝突,尤其是宗教文明之間的衝突,一直存在。在近代主權國家崛起之前,世界範圍內的衝突主要表現為宗教之間的衝突,尤其體現在「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1096-1291)是一系列在天主教教宗的准許下的戰爭,由西歐的封建領地主和騎士對被他們視為侵略者的伊斯蘭政權(地中海東岸)發動持續近200年的戰爭。
之後,歐洲內部在16、17和18世紀初經歷了一系列宗教戰爭。1517年新教的宗教改革開始後,戰爭擾亂了歐洲天主教國家或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政治秩序。
戰爭不僅體現為宗教衝突,還體現為叛亂、領土擴張和大國衝突。在30年戰爭(1618-1648)中,天主教的法國與新教勢力結盟,反對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儘管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而結束,但較小的宗教戰爭一直持續到1710年代,包括不列顛群島的三王國戰爭(1639-1651)、薩伏依──瓦爾登斯戰爭(1655–1690),以及西阿爾卑斯山的托根堡戰爭(1712)。

儘管隨着近代以來主權國家世俗化的強化,宗教色彩變得淡薄。但宗教從來沒有離開過戰爭,戰爭也一直在求助於宗教。世俗化是近代物質利益發展和商業理性的產物。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商業理性的崛起終於可以促使世界逃離基於宗教非理性之上的戰爭。既然商業世界可以通過正常的競爭而獲得利益,並且商業世界的競爭往往是雙贏的遊戲,那麼為什麼國家還需要訴諸於非理性的因素呢?不用說宗教了,連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態都不重要了(熊彼特的觀點)。
但這些論斷經不起經驗的考驗。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宗教戰爭亦然。宗教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如信仰、文明和文化等類宗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只要政治存在,宗教或者類宗教就會介入戰爭。
迄今,世俗化還在繼續,但宗教依然存在。實際上,人們很難排除世界再宗教化的可能性。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是人類。只要是人類,物質利益不可能完全取代宗教精神或者其它文化因素。在宗教文明中,西方是在世俗化方面走得最遠的,但現在西方本身已經出現了不適應。作為西方大本營的美國就是典型例子。
宗教政治是今天特朗普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再者,另一些從宗教轉向世俗的國家也出現不適應。土耳其是典型。自近代以來,土耳其走的是「世俗化」路線,但近幾十年來,土耳其走的是「再宗教化」路線。要意識到,這些都是主權國家的「宗教化」的趨勢。
如果考慮到宗教極端主義的崛起,那麼人們更沒有理由否定宗教政治的回歸了。儘管宗教極端主義的單位體現為非主權國家,但不僅其本身的崛起是政治所為,而且這些非主權國家的行為和主權國家的行為之間並沒有可見(或者人們能夠理解)的邊界。
文明衝突將取代宗教衝突
在當代,宗教戰爭這一論題因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一篇文章再次升溫。亨廷頓在《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1996年,此文章又被拓展為一本專著,取名為《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作者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
作者這裏所說的是產生於西方文明的兩種世俗意識形態,即西方基於絕對私有產權之上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和蘇聯基於絕對公有產權之上的計劃經濟意識形態。儘管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世界範圍內的大討論,作者也多被批評和攻擊。不過,這篇文章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主要原因還是直接指向了西方國家國際關係本質性的東西。

(Shutterstock)
歷史與複雜的西方國際關係
如果是物質利益主導一個國家的國際關係,那麼我們是可以度量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理性只是物質利益,那麼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外交行為是可以確定的。但是,一旦當宗教、文明和文化這些主導或者影響了一個國家的國際關係,那麼我們便失去了度量的依據;如果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僅僅是為了物質利益,更是為了不可度量的軟因素,那麼我們就很難確定這個國家的外交行為。
因此,我們對外在世界的國際關係存在太多未知,美國內部、西方國家之間(尤其是歐洲和美國之間)、美俄之間、伊斯蘭國家之間、伊朗與美國之間⋯⋯到底在發生什麼?很多事情往往出乎人們的意料,出乎意料就是因為不理解。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多得驚人:美國與歐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為什麼西方國家之間也發生衝突和戰爭(最典型的是一戰和二戰),但為什麼在對待非西方國家的時候又表現為團結?為什麼特朗普如此這般對待歐洲,歐洲還是那麼「傾心」於美國?為什麼歐洲國家不能和我們站在一起對抗美國?歐洲與俄羅斯是一種怎樣的關係?為什麼俄羅斯總是要加入西方,變成西方,而西方不接受俄羅斯?美國與俄羅斯是一種怎樣的關係?為什麼美俄雙方都會作出一些我們不能理解的行為,無論是鬥爭還是妥協?
我們更不知道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間的關係,除了我們觀察到它們兩者之間經常在發生衝突。我們不知道中東的海灣國家與伊朗之間的關係,也不知道伊朗和美國以如此「巧妙」的方式來互動?
很多人自以為理解這些,但充其量也只是假裝知道。實際上因為我們不知道,所以經常會犯判斷性錯誤。例如,為什麼最近在我們認為有利的形勢下召開的中歐峰會沒有取得人們所預期的成果?為什麼特朗普和普京一邊鬥爭激烈而一邊搞「親密」接觸?為什麼人們對美俄兩國的互動感到緊張,無論是鬥爭還是接觸?所有這一切,只是因為人們的不理解所致。
西方的國際關係呈現出物質和精神的交織、硬力量和軟力量的交織、世俗和宗教的交織,而這些交織又體現為一種幾乎神秘的「圈層」結構。這令很多時候,人們對此難以理解,更難以預測。

(白宮圖片)
五重圈層結構
特朗普第二任開始之後,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登拜登政府期間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國戰略倡議」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署名的文章。
這篇文章似乎可以給我們對西方的圈層結構提示點什麼。這兩位作者竭力反對特朗普的不再重視美國盟友的做法,警告特朗普政府不要「低估中國」,同時呼籲美國拉攏盟友,構建「新的聯盟」來對抗中國的挑戰。如果仔細閱讀,不難發現兩位作者所劃的圈層很是清楚的:第一圈是美英澳「奧克斯同盟」;第二圈是歐洲盟友;第三圈是俄羅斯(因為俄羅斯也是高加索白人文明的一部分);第四圈是高度西方化的非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和韓國;第五圈才是「其他」。
第一圈:美英澳「奧克斯同盟」;
第二圈:歐洲盟友;
第三圈:俄羅斯;
第四圈:高度西方化的非西方國家;
第五圈:其他。
中國是西方眼中的局外人
如果把中國置於這些西方的視角中間,那麼我們處於一個什麼樣的西方認同呢?中國是世俗文明,我們是世俗的哲學文明,不是宗教文明。這決定了我們是西方的「局外人」國家。
我們不是宗教文明傳統所說的「異教徒」,而是他們眼中的「非教徒」,為不同宗教文明所爭取的對象。或者說,我們不是宗教的敵人,宗教的敵人首先是另一個宗教,作為「非宗教」的我們是所有宗教想擴張的對象。這表明在國際政治上,我們不能簡單地在不同的「上帝」之間做選擇,一旦這樣做,我們就有可能真正成為其它宗教的「異教徒」,成為他們的敵人。
我們需要承認我們不理解西方或者基於其他宗教文明之上國家的國際關係及其外交行為,更不能被西方所創造的、只體現表象的國際關係和外交理論所迷惑,而被西方牽着鼻子走。我們只有在承認不理解的基礎之上,再去理解它們的行為。這樣做是為了對國際政治格局具有一個準確的判斷,避免迷失方向,從而把自己置於不敗之地。
如果從世俗和宗教兩分法來看,人們可以預見今後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兩個「中國」:一個是形式性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中國,即一個接近或者已經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着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一個是實質性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中國,即一個對宗教文明國家來說又近但又很遠,又熟悉但又陌生的「局外人」國家。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局外人國家(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