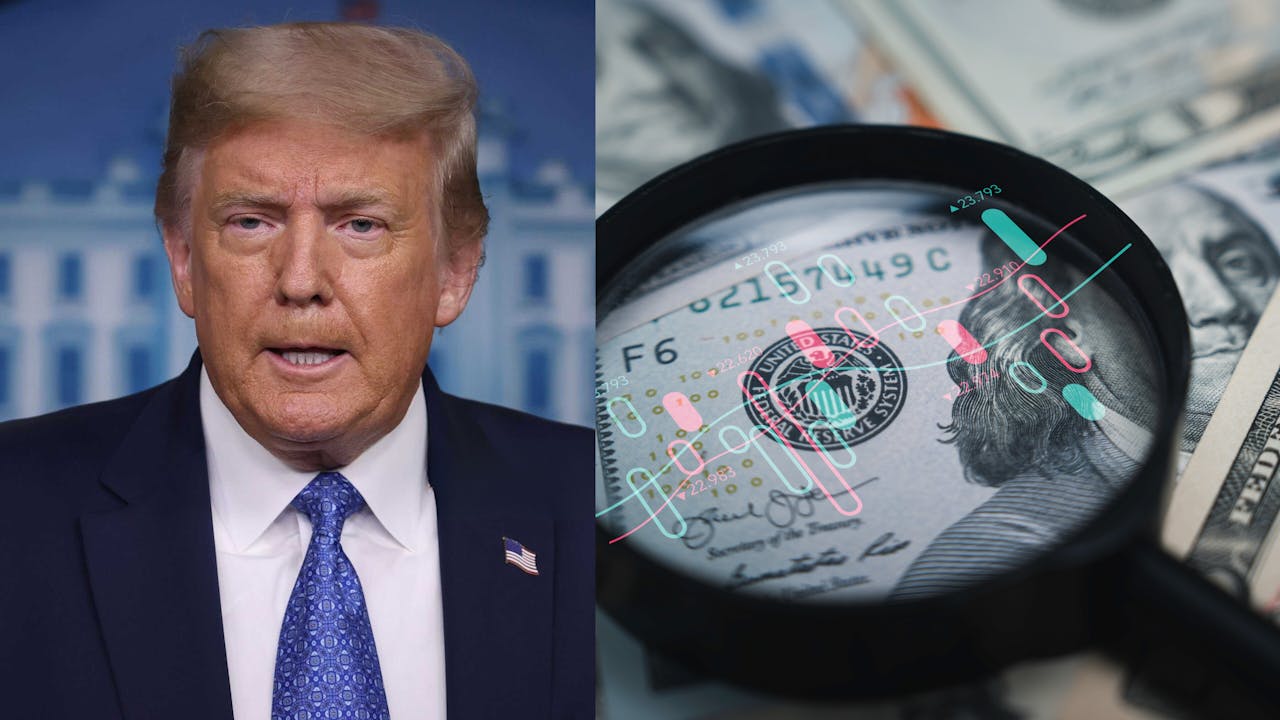特朗普再次回歸給全球帶來的最大不確定性就是未來的世界是否還是開放的,或者借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著《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話來說,世界是否繼續是平的?
「超級全球化」與財富分配問題
過去數十年里,世界經歷了一波很多經濟學家所說的「超級全球化」,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範圍內相對自由地流動。隨着開放源代碼、外包、離岸生產、供應鏈和搜索技術等新動力的產生,世界被鏟「平」了。這個過程大大促進了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為全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但是正因為世界變「平」了,在市場機制的能量被充分發揮出來的同時,各國的內部財富和各國之間的財富分配出現了巨大的變動。就財富的內部分配來說,巨量的財富流向了那些主導全球化的小部分社會群體(主要是資本)手中,那些有能力參與全球化的社會群體也獲得了一些利益,而那些沒有能力參與或者被排擠出全球化的社會群體不僅沒有能夠受益反而成為了受害者。就財富的外部分配來說,全球化產生了「拉平」現象,即那些有能力參與全球化甚至主導全球化的國家變得富裕起來,而那些沒有能力參與全球化或者沒有能力抵禦全球化衝擊的國家變得貧困。這也就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全球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內部和國際根源。

(前海管理局)
全球化面臨挑戰與悲觀情緒蔓延
今天,各種因素影響着全球化,包括大國間的地緣政治較量、區域衝突、關稅主義和貿易戰爭等。全球營商環境日益惡化,愈來愈多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成為關鍵問題。這使得愈來愈多的人對前途感到異常的悲觀。在過去數十年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現在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體。這一代人在過去的「好時光」中長大,「好時光」對他們來說是常態,但現在「好時光」已經過去,並且不知道如何應付一個未卜的前途,悲觀情緒蔓延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麼,人們真的需要那麼悲觀嗎?此刻,人類的交流理性或者溝通理性顯得特別的重要。如果悲觀導向了理性,那麼前途並不會那麼壞;但如果深陷悲觀而不能自拔,導向了躺平或者放棄,那麼就很難說有前途了。近日(2025年1月20日),我們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了題為「開放合作·可持續發展」(BEING OPEN·BEING SUSTAINABLE)的海納講座圓桌論壇,邀請了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國際顧問Jeffrey Sachs,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科技大學校董會主席、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研究院理事長沈向洋,中國科學院院士、深圳醫學科學院創始院長、深圳灣實驗室主任顏寧,從交叉學科的角度來探討開放、國際合作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作為主持人,我和各位嘉賓做了充分的溝通和交流,感觸良多。我的總體結論是,與其說對環境感到悲觀,倒不如轉向以個體或者集體的行動去改變目前的環境,這樣才可以實現存在主義式的目標,即不讓環境來定義人的本質,而是相反。

同球共濟的世界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近代以來,開放幾乎就是全球化的代名詞。無論是被動開放還是主動開放,開放塑造了全球化,各國也都捲入全球化。儘管很多國家在發展的早期都會經歷一段相當長時間的重商主義,以保護民族產業的發展,但最終都必須加入全球化的行列。經驗地看,加入全球化不能自動保證一個經濟體變得富有,但一個經濟體如果一直處於孤立狀態,那麼是沒有任何變得富有的可能性的。
過去數十年的超級全球化塑造了今天同球共濟的局面,愈來愈多的國家相互關聯和互相依賴,我們用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形容今天的世界。也正因為如此,國際合作變得日益重要。在全球性問題面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全球性問題。尤其是對較小國家來說,它們面對全球性問題,更是束手無策。例如,就氣候變化而言,如果海平面上升的情況得不到改變,諸多海洋小國就會消失。
但是現實情況是,每當一個國家遇到內部發展問題的時候,或者當感到對外部國際環境無能為力的時候,往往轉向「內向」,趨向於孤立主義和封閉。現在,即使像美國那樣曾經如此開放的國家也轉向了自我保護主義。這使得全球整體上陷入危機之中。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如何讓各國政治領袖相信封閉不僅不利於自己,也不利於國際社會?如何讓大國政治領袖相信大國在提供國際公共品上承擔着特殊的責任?這些是我向Jeffrey Sachs提的問題。
開放、國際合作與可持續發展的探討
正如中國老話所說,「方法總比困難多」。在現有的全球化遇到困難與挑戰的時候,也有很多積極的因素在出現。美國曾經一個是開放開源的國家,尤其在二戰之後,為世界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現在內部出現了問題,特別在國際層面迷失於地緣政治的意識形態之中。特朗普的再次回歸更使人看不清美國如何走出現在的困局。但正如Jeffrey Sachs所表示的,下一步中國的國際角色變得重要起來。中國已經成為製造行業的領軍國家,特別是效率很高,綠色技術發展很好,不管是電動車還是5G、可再生能源、能源轉型等,中國都在引領全球。Jeffrey Sachs尤其欣賞中國提出的三大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所有這些可以促進技術界、學界、商界之間更深更廣的合作,推進「技術共享」和開放、開源。

科學需要開放和全球化
科學更是需要開放和全球化。沈向洋觀察到,互聯網的普及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學術資源的共享,使得學術信息的獲取更加便捷,從而加速了全球科技的進步。開源技術的興起,對科學技術的跨界合作意義非凡。開放的學界合作、跨界或者是跨境的人才培養,也會反向助推科技和經濟發展。同時,類似人工智能技術對人類構成的挑戰甚至威脅也迫切需要國家間的合作。
顏寧表示,儘管不時地遇到困難,但科學界的合作從未被打斷,科學家之間總是在不斷地進行對話。特別是在生物學領域,國際合作更是常態。顏寧也強調了中國開放的關鍵作用。當美國轉向封閉的時候,中國的科學界不僅必須保持開放,還要更開放。例如,她所領導的深圳醫學科學院不僅要做臨床研究和醫學轉化,更要充當一座國際溝通的橋梁,成為一個開放的國際合作平台。
實際上的確如此。如果人們僅僅把眼光置於政府間的合作,那麼就會覺得悲觀。但如果超越政府,那麼看法就會很不一樣了。政府當然重要,各國政府對國際合作的態度深刻影響着國際合作,但是政府並非是唯一的國際角色,尤其在全球化時代和社交媒體時代。美國之所以變得強大就是因為其開放,開放塑造了美國的教育人才系統、企業系統和金融系統,使得美國能夠吸引和匯集全世界優秀科研人才、優秀企業家和優質資本。但這些並非都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所為,大都是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的行動所致。直至今天,當美國政府奉行保護主義的時候,科學界反而一直在致力於推動國際合作。

社會力量與全球意識
最近美國的「抖音難民」湧入中國小紅書事件也從另一個角度彰顯了自下而上社會力量的能量。當美國方面要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禁止TikTok」在美國運作的時候,美國抖音用戶就轉向使用小紅書。這一事件也促成了美國方面對TikTok的重新思考。
其實,現在各國的人民已經擁有了全球意識。一旦當一個國家過於自私而使用各種「國家的理由」出台不利於人民利益的政策的時候,很多人都會選擇出走。當特朗普第一次當選總統的時候,很多人因為不滿其政策而離開了美國。過去幾年,因為美國政府對科學家的打壓而促成了一些科學家離開美國。資本和企業家更是如此。類似的自下而上的力量往往會促成政府政策的改變。例如,儘管美國白人至上的原教旨主義者反對一切移民,但考慮到技術人才對美國的重要性,特朗普也在改變對移民的態度,促成不對所有移民實行一刀切的政策。
就世界發展大趨勢而言,開放不僅僅是各國的發展所需,開放更是人性的內在本質。誠如亞當·斯密所觀察到的,交易是人的本性,而開放則是交易的前提,不開放,交易就不會發生。歷史上看,凡是符合人性的政策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會成功,而違背人性的政策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會失敗。
二之一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