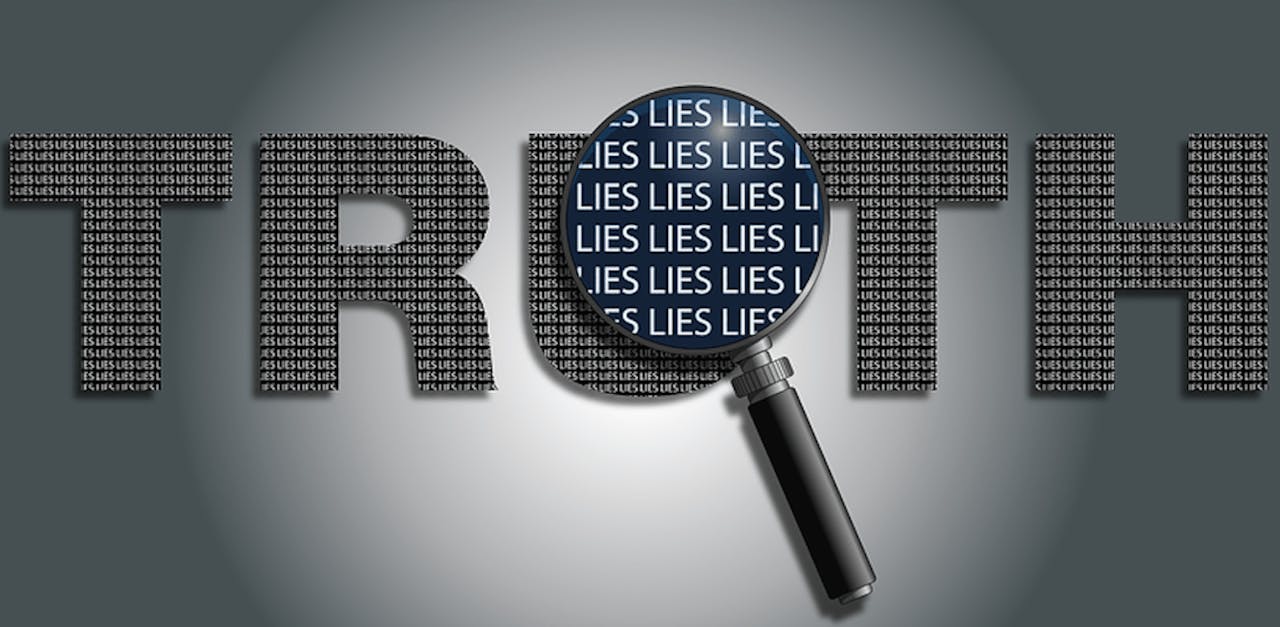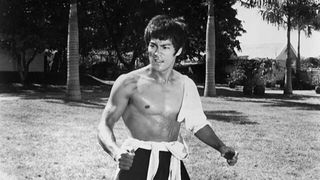不知是從哪時開始,有人爭論香港的教育,到底應該培養批判思維,抑或身份認同。這兩種選擇並不對立,甚至不應該設定成選擇。二者的關係明明糾纏一起,只是有人有興趣去檢視、分明。
思維不是寡頭的,你總是先置身於一個身份,有了一個「立場」,才開始思考;那是一種「對自我特性的認定和歸類」。因此,有認為身份認同比批判思考更形重要,因為那是為人的根本,是認識世界的「立足點」,這甚至框定了你的思維方式。言下之意,你所認同的價值體系,決定或大大模塑你對家、國和存在位置的認知內容。如此思考的人,會認為思想方法只是工具,用以「調整」自己的角色,並從這個角色獲取所認定的答案。我是一個慕道者、傳道者,抑或衞道者?同道中人的角色也有差異。
至於批判思維能否超越國家、種族、性別與階級的考慮,它得怎樣獨立,才使我們得到自由或更能接近真理,其超然的地位已經受到動搖。但批判思維的衞道之士,必然是強悍的,甚至日益在政治是非黑白的情境中,感到任重道遠,主張要清晰反思自己各式各樣的身份認同,三思標準答案。口號是「批評若不自由,讚美便無意義」。
真理有特殊性
有關討論,令我想起牟宗三在《中國哲學十九講》中的第二講,題為〈兩種真理以及其普遍性不同〉。文中率先談到真理有普遍性,亦有特殊性,特殊性在於從一個「通孔」裏所呈現的真理,說的是文化和身份的「通孔」。如此出現了真理的多樣性。牟先生引述羅素的「外延性原則」;說外延的知識是不繫屬於主體而可以客觀地肯斷的;但他更重視內延性的真理。
內延真理離不開主觀的態度。小說家、詩人和宗教家,他們主觀的見地裏有真實感,是人生世相的真實性。牟說文學家的主體性是情感,而宗教家乃至儒家所講的,亦有箇中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不是科學式的理性,而是「道」。「道」是唐君毅先生所說的「啟發語言」,表現的是生命的一種「澄明」。牟說一切道德宗教都在這個「明」的範圍內,這個明不只是來滿足我們的情感的,也不是科學。
牟先生常說主體是不能對象化的。他不只是說不應該,而是不能夠;因為主體能表現價值、判斷是非,把人恢復為人,見出個人體會的真理。
有趣的是,牟說沒有所謂英國的科學、中國的科學,又沒有所謂中國的儒家、或西方的儒家;不同不是那個內容的不同,而是表面「跡象」的不同。這裏所謂跡象,其殊相實屬表層,有時是主體以自身的體會來調節和調整自己的文化,生命的態度,而非批判思維。例如中國人學科學聰明者不少,但必須有外延性的思維,否則科學永遠進不來,民主政治也一樣。
西方人學中國哲學,同樣必須正視箇中的內延性真理,即要和自己的生命叩連起來,這才能說「明」。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