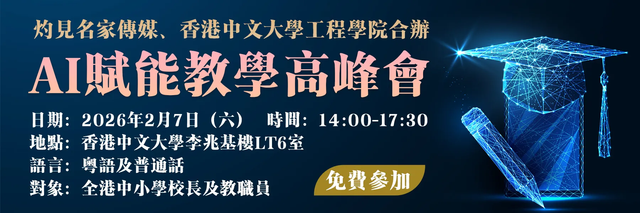羅孚先生去世整10年了。我父親是羅先生同事,兩個人並排坐在報社的辦公桌前,那是超過半世紀以前,報社還沒有冷氣,夏天的時候,兩個人都脫了襯衣,上身穿一件小汗衫,在攝氏30多、40多度的室內揮汗如雨、揮筆疾寫。我自從出生就經常聽見父母講「老羅,老羅」,「老羅」是父母最尊敬的朋友,後來「長大以後」,有資格跟父親去報館「玩」,打兵乓球,父親鄭重地牽着我的手去拜見「羅伯伯」,指着我的頭說這是老五,叫小不點,從此以後我就成了羅伯伯的小不點,從小學叫到60多歲,一直到羅伯伯去世以前。
報館不時舉辦家屬活動,孩子們都很嚮往,報館在南灣有一個泳室, 這是夏天必須去的聖地,報慶的時候當然舉辦慶祝活動。有一次,負責節目的一位報社叔叔把我們 一群幾十個孫猴子排成兩條競賽隊伍,這位叔叔把一句話悄悄耳語給第一個孫猴子,要求我們也用耳語把這句話一個傳一個,傳到最後一個大聲講出內容,看那一隊人最快,我排在中間靠後面,前面的孫猴子在我耳邊飛快講了一句話,其實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他講什麼,我只聽到一堆奇怪的音節,就照樣把這堆音節傳給下一個,到了最後,我們這一隊大勝,但結果還是輸了,很簡單,輸了的一隊明明白白的傳了一句話,大意是「慶祝報社多少周年報慶」,我們的一句話則是「#$%&*! @&&」 ── 不知所謂!

羅伯伯很幽默,很有童心,這故事還得從頭講起。
1966年底我14歲,是香港一家愛國學校的中學生,我大哥則在廣州暨南大學念書,一天他來信說,有幾個從新疆來廣州串聯的維族年輕人要回烏魯木齊,忽悠他同游新疆,我大哥立馬也忽悠我同去,得到父母同意後,我歡天喜地到暨南大學與大哥匯合,隨兩位維族小夥子踏上難忘之旅。時逢文化大革命串聯尾聲,串聯者必須按照規定回原單位,維族小夥子在我的香港學生證上塗抹了一個新疆名字── 阿不拉提,每逢遇上查票,把我的漢人臉塞到他懷裏藏起,只推說「阿不拉提病了」,驚心動魄瞞過乘警。
6天6夜之後我們到了烏魯木齊,「打倒王恩茂!」的標語觸目可見,王恩茂是當時新疆黨委第一書記──我的新疆故事暫時到此為止,現在回到羅伯伯身邊。我父親把我去新疆的事私下匯報了羅伯伯,因為這不是正常活動,所以屬於「保密」,我回到學校也很沉得住氣,不曾向一個同學吹牛,後來,在報社的活動上我又遇到了羅伯伯,他看見我就衝過來,彎下腰湊近我耳朵,一手遮擋住自己下半邊臉,用重口音廣東話向我悄悄耳語:「王恩茂搵你啊!」說完,打個眼色就跑了,留下我在心中默默回味,一直回味到超過半世紀後的今天,有如一杯醇厚的老茅台,時間只會增加芬香。
說到羅伯伯,怎麼少得了老酒,有一個晚上,羅伯伯和我父親在飯館小聚,旁邊還有好幾位尊敬的客人,大家舉杯喝茅台,當然除了我這個小不點,我被冷待遇了,就放出一句冷話,說這酒很辣,羅伯伯咂咂嘴說,不辣,不辣,說時遲那時快,他拿起桌上的辣醬倒幾滴在他的茅台杯子裏,一口悶了,再咂咂嘴說,不辣,不辣,甜的⋯⋯!
說到這裏,我很想喝茅台,我現在可以喝了,我要回到當晚那個小聚,向先輩們磕個頭問好,說,這茅台,真的很甜哦!
(羅伯伯在2014年5月2日去世,我父親嚴慶澍在1981年11月26日去世。另外,茅台在70年代才不到十元,80年代「嚴重漲價」到一百多元,現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