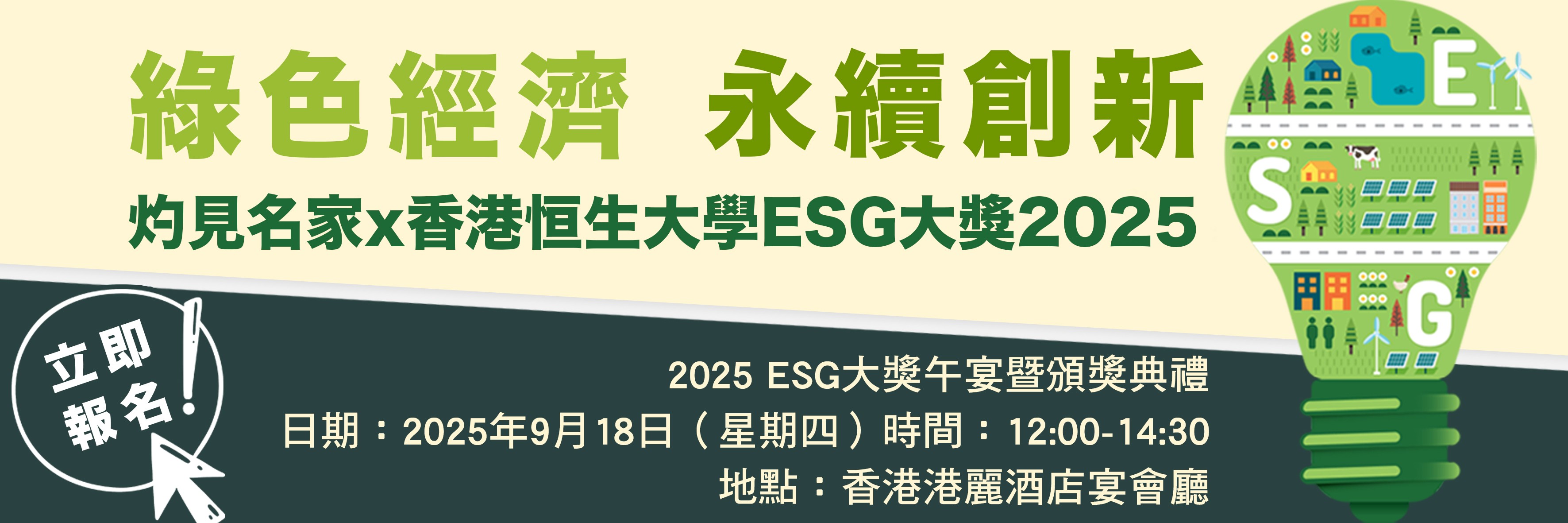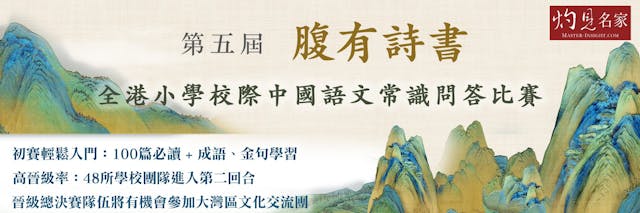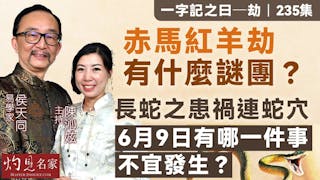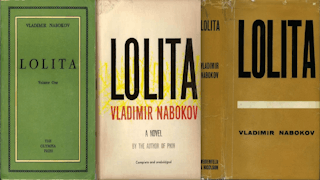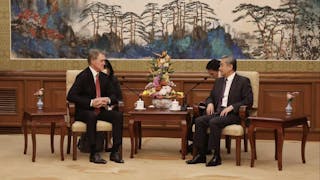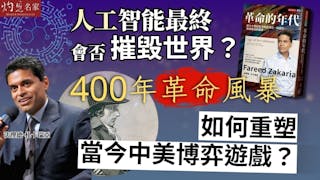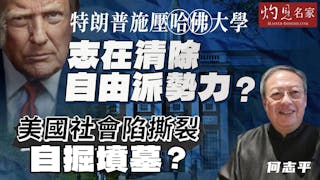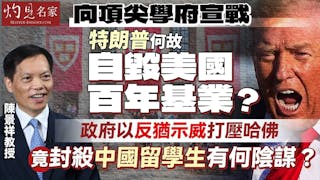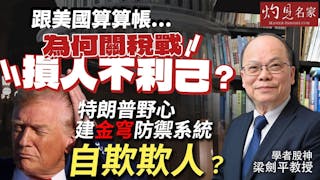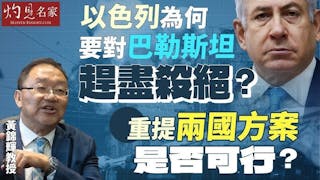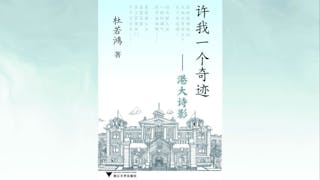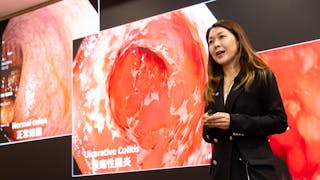編按:本文為作者在今年11月1-2日香港話劇團舉辦「劇場與文學」戲劇研討會發言部分內容。
話劇發展在漢語語境原本與文學發展一脈相承,互動互生。中國傳統戲曲曲本一直被視為文學作品來閱讀。西方文論視劇本與詩、小說為三大文學體裁。古希臘更視戲劇脫生自宗教,與文學同源。元雜劇本身就已非單純的戲劇演出,還包含清唱、舞蹈、雜技、院本(唱優的腳本)與打散的混合演出形式,至今未能窺看其現場表演,文人才士的雜劇本卻以文學留傳,傳統戲曲的文學性反取代當時即時性的表演。可見劇本兼具演出文本與文學讀本兩可的價值。
五四的文學運動更是中國話劇突破唱戲舞台傳統的類型開拓的背景場域。1907年春柳社在東京演出,成為話劇的濫觴,同時在上海蘭心大劇院春陽社演的《黑奴籲天錄》,奠定新劇的地位。可見劇場的改革與文學改革的孿生關係。《茶館》以小說手法創作劇本,開拓新的布局形式結構,可惜這話劇結構發展下來,逐漸去除中國傳統劇場兼具唱造唸打中的唱、打的部分,同時也忽略傳統戲曲中虛擬舞台的美學元素,跟從者使劇本結構模式狹窄,倒反而在後來限制了戲劇場的發展。
劇場鮮見改編本地文學作品
文學「搬演」其實也不限於文字文本的改編。若把民間傳奇、經典神話、這些民間文學或口頭文學重構成劇本,是文學進入劇場的傳統進路,廣泛見於傳統戲曲舞台,甚至編成大型舞劇,例如:梁祝故事曾分別改編成舞台劇、芭蕾舞劇、粵劇、越劇,甚至大型舞劇亦可見一班。歷史人物這類題材進入劇場,歷來重構文本繁多,故幾乎視為文本換轉(transfer),或也可視為歷史文本改編。事實上,在70年代之後把中國現代小說作品改編成劇本亦屢見不鮮,只是改編本地的文學作品卻鮮見。當中有一件有趣的事:1972年劉紹銘編台灣作家《陳映真選集》,由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向香港讀者介紹他的小說,比他在台灣出版《將軍族》(台北:遠景出版社,1975)還要早。1978年致群劇社搬演黃春明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和陳映真的《夜行貨車》,1981年上演《將軍族》,比1983年台灣把《兒子的大玩偶》小說拍成電影還早。可見文學與劇場的關係延及台灣文藝的發展。
陳麗音提倡重視戲劇的文學性
另一方面,不知怎的,在香港的文壇,自70年代大會堂的興建與香港話劇團的成立,隨着劇壇開始邁向專業化,更廣泛的引進和編譯不同流派的西方劇作,本地原創劇本愈隨之而勃興,文學現身劇場或彼此的互動反而愈不多見。劇作家兼戲劇研究者陳麗音是少有提倡重視戲劇的文學性的劇場作家,並從事劇本編印的工作。她提出香港劇壇不重視香港戲劇的文學性,歷來重要的藝術節以表演藝術為重,文學項目缺席。歷來看過劇本的人一定比看戲的人多,但香港看劇的比讀劇本的人多。她痛責香港戲劇藝術遠遠超過文學藝術發展這個不健康現象。

香港文學界與劇場疏離
近年喜見表演藝術團體和藝術節也開始留意文學的項目,進劇場、浪人劇場皆為努力轉化文學為戲劇表演的劇團,但只有後者採香港文學。前進進也曾改編文學演出而屢見成績。有人認為劇壇所選演的香港文學作家有頗大的傾向性。其實,香港文學界與劇場疏離,劇壇也不願與香港文學人交手,與文壇部分人的錯誤取態有關:有人把文學作品改編視為戲劇宣傳香港文學的一種包裝或推廣手法。不少文學讀者及文學人對小說搬演,仍然帶着對文學作品既有的感情投射和詮釋定向入場,觀看改編作品仍堅持要求在劇場尋找原著的文字,一字一句易不得,在這些可見的元素下影響文學進入劇場的方向,造成觀賞的干擾,不能持平抽離地把以文學文本作為創作原型的劇作視為獨立的戲劇作品;又或者有時編者過分拘泥於貼近原著的文字風格和結構語序,也會障礙舞台表演功能的發揮。界內出版了不少劇本,但把劇本視為文學文本研究,一方面未能在文學界普及,另一方面文學教育雖有劇本作課文,多數着重文字技巧、人物塑造等文學分析,較少把作為表演文本的獨特性與文學性並舉來研究。
孿生兄弟何時相認?
想1944年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收入她第一本小說集《傳奇》,翌年馬上親自改編成劇本,在上海蘭心劇院公演40多場,盛況一時無兩,突顯文學與劇場的互動光輝。香港作家很少兼擅劇本創作,目前既能編劇、本身又有文學創作的作家有黃國鉅、盧偉力、謝傲霜、黃碧雲等,惜未能構成風氣。文學與劇場這對孿生兄弟何時相認?這恐怕要在更多的互動共生,從彼此差異中拉開,發現藝術形式更大的可能性和共融性,才能迸射出獨自存在所未見的光芒。
圖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