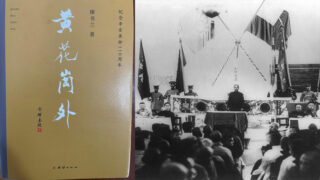在過去廿年間有江湖傳聞,孫中山曾經流落美國,潦倒到要在餐館「洗大餅」(做洗碗碟工作,西餐餐碟形似大餅),時為武昌起義當日(1911年10月10日),不少人信以為真,更有傳媒「名嘴」多番公開重述此則訛聞。試想想,當時已是4、50歲的革命老將、且有西醫學歷及實際醫生工作經驗的孫中山,會為了生計在餐館「洗大餅」?
以訛傳訛 籌款變成「洗大餅」
始作俑者是美籍唐德剛教授(1920-2009),他的散文隨筆集《晚清七十年》(遠流,1998,主要是1990年代他在臺灣發表過的文章),當中對孫氏有頗大篇幅的辛辣評論。最要命的是,唐教授「隨便隨筆」且繪形繪聲(有台詞、道具、走場動作),複述了好友盧琪新的家族故事:話說武昌起義當日,「老孫」正流落在美國內陸小鎮丹佛(Denver),在盧父(瑞連)開的一間餐館打工當企檯(餐館侍應)。後來以訛傳訛,有人再貶多一級,企檯變成「洗大餅」!
已有考究(習賢德、封從德、沈衛紅等)指出唐教授資料有誤,孫氏在武昌起義當日,是在奧格登(Odgen)小鎮,且有信件為證,稍後才到丹佛。只不過,這點尚未能推翻唐氏大砲之言,因孫中山最終確有到過丹佛,教授仍可說「老孫」有在盧家餐館打工之可能。關鍵不在乎日期上的差誤,而是在於孫中山此時的行蹤,他為何會去丹佛?
1911當年,是清王朝氣數已盡、奄奄一息之際,光緒與慈禧已在兩年前相繼死去,由三歲的溥儀繼位,是年4月便是轟轟烈烈的黃花崗之役,6個月後便是武昌起義了。孫中山此際是為了配合國內的武裝行動,巡迴加美兩國百多個城鎮(孫本人在此行到過約卅多個城鎮),為革命大力籌款,給予清王朝致命的一擊,2月至4月間(黃花崗之役同時)在加拿大共籌得11多萬加元,9月、10月兩個月在美國更籌得14多萬美元。孫中山只是途經丹佛,並不是短或長住。下圖是筆者綜合各方史料,繪出孫氏當年的籌款行程:
當年汽車和公路尚未普及,跑埠主要靠火車、馬車或內河船,行程極度緊湊,每站的停留時間平均只得一兩天,亦要開台演說,在丹佛的兩晚一日中,便要在一間「中國戲院」發表演說,何來會有時間去餐館打工?籌款活動是大隊人馬,丹佛一站亦不例外,「老孫」離大隊獨自去做半日企檯,天方夜譚!
孫中山此行是經過周詳策劃的,旅費是得到洪門籌餉局全力資助,經濟上絕無問題,動身前已用了多月時間在美國西岸做準備功夫,包括聯絡各地洪門分會,且以洪門總會名義,大事廣登華文報紙預告行程(當年舊金山報紙,行銷美加各地華埠),所到之處,皆有當地洪門手足照顧,在各大埠必安排多晚在酒家設宴與華僑聚餐、在會堂公開演說,個別城鎮更有華僑群眾和儀仗隊在火車站迎送。
清廷一直高價懸賞孫文的人頭,此際經黃花崗一役便更然,而亦有足夠史料顯示,當時連康有為之流,亦可能對他有殺機,為了人身安全,洪門中人便精選貼身保鏢給孫全程護航,單是保鏢費用,加國一程便高達平均每日65加元(黎全恩教授語),事後孫亦有信函(1911年5月7日)回謝加國保鏢之一謝秋。是次美國之旅,更有黃芸蘇(1882-1974)全程陪伴打點一切,黃是台山華僑,亦是當時美國同盟會和洪門籌餉局負責人之一,日後會隨孫回國服務、且成為國府要員。
孫中山所到之處,多下榻當地高級旅館,每日房租高達2至5美元,在丹佛住的更是頂級豪華大酒店 Brown Palace Hotel,當年美國塔虎脫(Taft)總統,便剛在一星期前「落難」於此。該酒店今仍是丹佛頂級名店,內有展出昔日孫氏停留的文物,包括入住登記資料。而各地熱心華僑,亦曾多次贈予孫氏過百元之程儀/盤川,他便將此額外捐贈撥歸革命軍餉。在丹佛的「中國戲院」演說一次,孫中山便能籌得1000美元,唐教授筆下那位「老孫」在餐館打工一天,以當年標準工資計,只得一大美元而已!打工之說,不攻自破。
大膽假設有餘 小心求証不足
丹佛的舊唐人街早已湮沒,該市華人人口不大,現亦無個像樣的華埠,當地華人史料更蕩然無存。盧琪新的家族傳聞,只是個美麗的誤會,唐教授亦無相片或出粮單據以茲證明。孫文如真的要落難在美國,他的第二故鄉夏威夷應是首選,雖然孫眉已於年前回流返香港,但檀島乃孫中山成長和熟諳之地,和仍有眾多家境不俗的親友可投靠(美國本土不是、更何況是內陸小鎮),且只他一個人,生活費用有限,絕無在唐餐館當企檯或「洗大餅」之必要,如真的要賺取外快,當可在唐人街無牌行醫。
其實,盧琪新之弟盧琪沃牧師(曾在臺北的凱歌堂擔任神職工作,該教堂是蔣介石夫婦做禮拜的專堂),在《晚清七十年》出版前十多年,已披露了一個較合理和可信的故事版本(《孫中山與美國》,習賢德,上海人文,2008,盧牧師版本已於1986年公開),孫中山與盧瑞連是香山舊識,更可能是親戚(唐德剛語),孫只不過曾在盧家餐館用午膳,而由於時間倉促,婉謝了盧為他設宴洗塵/慶功之好意。盧琪沃更清楚憶述,孫中山在領眾祈禱時,特意引用新約聖經腓立比書第四章、第六和七節,感謝神的恩賜。
綜合上述各點,足見唐氏此則傳聞荒謬之處,「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証」嚴重不足,可見學術權威亦不可隨便輕信。孫中山史料汗牛充棟,唐教授無可能不懂得考證,他更在《晚清七十年》的自序中,煞有介事引其恩師胡適的名言『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這次唐教授是胡塗了,只有半點證據,便說了十二分話!
唐教授的大作不是人人讀到,但傳媒「名嘴」對公眾、尤其是對年輕一輩影響深遠,他把教授的遊戲文章當作真理,自己無做考証便人云亦云,更不斷在傳媒上復述此說,這是違背了一個知識學人的良知、一個傳媒人應有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