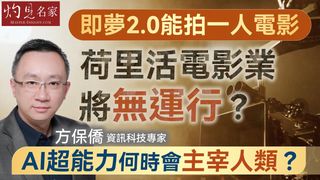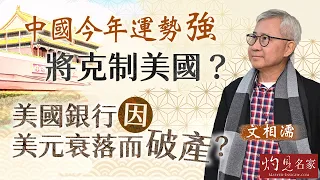香港被形容為飛龍,若要問小龍如何起動,歷史給的答案顯然不在於千禧年代的金融股市,而是在於更早、更底層的支柱。這比喻原本指向製造業、港口和地產業,以及其背靠的七、八十年代的騰躍動力。在那些沒有被寫進年報的清晨與深夜,有一整代人,把青春交給了這座城市。
借來的時間
七、八十年代的打工仔,跟戰後攜帶資本與網絡南來的人不同,他們多在1969年後南移,匆忙之間沒有反覆衡量得失、試錯回撤的選項,更多時候是一種被歷史擠迫、忐忑中出走的遷徙。原本可依賴的學位專業、倫理網絡均一夕作廢。小島並不承諾未來,只是暫時的容納、借來的時間。不少人牽着孩子,揣着對未知的注碼,就這樣帶着那副準備被消耗的軀殼南渡。
這群曾被喚作「阿燦」的新港人很快明白,在這座城市,生存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曠日彌久的消耗與磨蝕。本來在國內一、二綫城市是知識分子或專業司職,現在來到城東的觀塘及九龍灣,或城西的葵涌或荃灣,身份地位迅速下沉。製衣廠的流水線、紗廠裏染印的緞子,佔據了他們生活的鐘點。996是基本盤,之外還第二班,完了也許還有臨時的,那才叫無縫的連接。
當中有感知到外語的作用的,把它視為第一道需要跨越的門檻。它不是社交修辭,也不是文化品味,而是為了讓自己的名字寫在每天的打工卡上。不少人在工廠下班後,到夜學一字一句地對照字典;也有人在擠迫的板間木屋裏,把報紙當教材,間中還有流浪的野貓作伴。
這一代人知道,教育未必能立即改變階級,卻可能豐富下一代的選擇。他們會把有限的資源,讓孩子上興趣班,如由同為新移民開的繪畫班、鋼琴班,投注在下一代尚未成形的可能性上。這些「奢侈」的消費,背後沒有什麼浪漫的期望,更像是一種近乎本能的承擔,只要孩子多學一門,世界或許會少一扇對他們關上的門。
這一代人很少談論生活平衡和品味,因為休息並不在選項之中。當退路缺席,咬牙便成為唯一可控的。這種態度,常被解讀為無知、甚至冷漠,卻忽略了那其實是一種在歷史大潮中求存的回應方式。

築巢落腳
他們後來在小島建立如《織巢》般的感情,亦非即時的生成。起初,這裏只是暫時的棲息處,是下一步尚未出現前的停靠點。但時間具有黏性,當孩子漸漸長大,當生活細節在保姆車上、孩子踢球的場邊反覆出現,當通勤地點一路上流到銅鑼灣、郵寄地址開始有了自己的名字、家俱漸漸有訂製的彎角、鋼琴的餘音開始飽滿客廳⋯⋯歸屬感並不需要面書帖文來證明,而是由無數次從學校訓導處往返時的心力交瘁和深夜在家課冊的紅字旁簽字時的憂心忡忡,慢慢織成。
今天,那一代築巢者正在一個個、靜靜地離場,沒有太多的交接儀式和禮讚。辦公室的冷氣工程仍照常運作,球場仍聽到揮拍聲。
巢根交錯,承托仍在。他們未必被史冊記住姓名,也未必說過什麼漂亮宏大的話,但他們曾燃燒的生命,在城市的脈絡中留下點點烙印。沒有以「建設者」自居的一代人,卻讓鳥巢得以穩固,讓後來者可以在其中試飛展翅。
若說小龍在七、八十年代完成了一次經濟起飛,那麼讓牠得以振翼的起跳台,並非什麼奇蹟,其實是那一代人一枝一葉的築織。(寫給我們的父母親)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