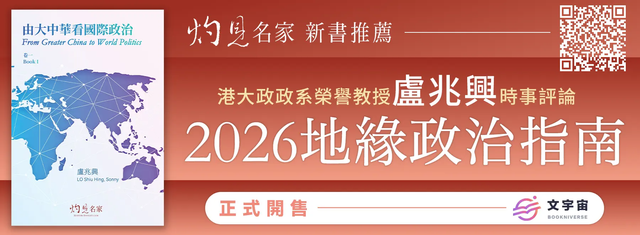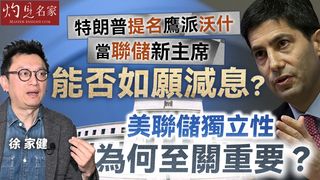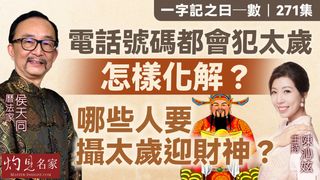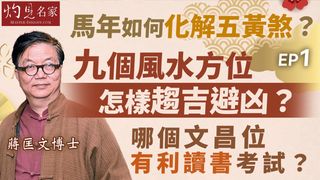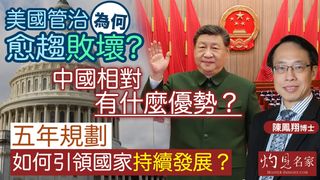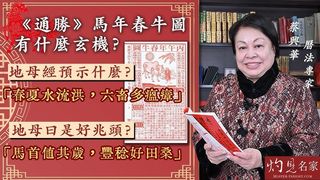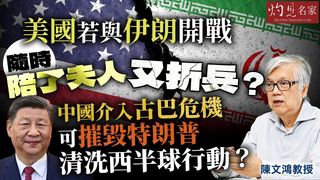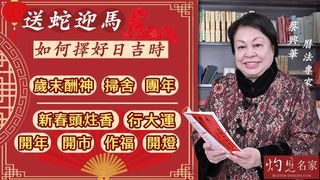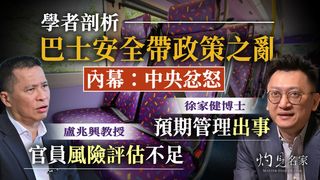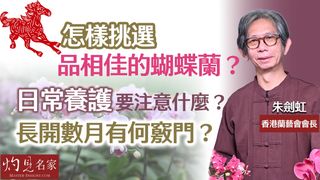編按:近日寶能投資集團大規模收購萬科企業的股份,更成為最大股東,萬科卻於12月23日發表歡迎安邦保險成為重要股東的聲明,事況引人懸念。適逢香港科技大學(科大)25周年誌慶,於10月份舉辦25周年傑出人士講座,邀得萬科創辦人及董事會主席王石擔任主講嘉賓。
王石幽默風趣,善於鋪敘,在席者屏息傾聽,滿座為之生輝。本社謹將講座發言整理成文,讓讀者了解王石的為人與理念,如睹其人風采。全文分四部分:
一、王石與香港的緣份、對中港關係的感受
二、第一次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驚險經歷、啟發
三、第二次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體會
四、對賽艇的體會
本文為第一、二部分。第三、四部分見此。
整理:何敏盈
(一)
我這次接受香港科技大學(科大)邀請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科大在亞洲排名第一,第二因為陳慧珠女士(科大商學院前副院長,編按)很有誠意。幾年前我在台灣講演,她來請我去科大教書。我問她為什麼不來深圳找我,要老遠來台灣。她說在深圳很難找得到我。其實我最希望還是到大學講課,不是講演。因為講演是不收費的,無論講得好不好,人家都會給你鼓掌。講課可能總共要講16個小時、兩天半,而且是要付費的。學生來聽你的課,如果講得不好,他們會刺你。(眾笑)講演,交流少一些,更多是付出。教學可以跟學生交流更多,收穫更大。少年、中年時代,我很嚮往成為教授,在大學講課。雖然有這種想法,但國內來說,清華、北大這些名校,我們這種企業家,往往只可以去做一個講演而已。我卻希望更多的去講課。
與香港緣深 理解香港心情
我在大學的教學生涯是在科大開始的,給我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印象。我希望60歲至70歲,有更多的經歷用在學校。所以我2010年到過科大做客座教授後,2011年1月份又去了哈佛大學進修,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總結自己的經驗。我不希望講自己的故事很好聽、講得很興奮,大家也聽得很興奮,但過後就都忘了。
在科大教了一年書之後,我知道應該如何在大學教書,於是也接受邀請,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書,課程是《企業倫理》。後來周其仁教授邀請我去國家經濟研究院,參與一個活動。參加完了,周教授說給我一個聘書,我就接受了。兩年前新加玻國立大學商學院又把我聘進去。科大第一次聘用我是一年,第二次聘兩年。我的教學是在科大開始的,在此我表示感謝。(鞠躬,眾鼓掌)
我創業和香港是什麼關係呢?我1983年到深圳,1988年萬科股份改造,顧問公司就是香港的新鴻基證劵公司。這個公司已經不存在,當時屬於本土企業,做得相當大。萬科的五個發起股東,除了我,全都是香港人。這裏不妨介紹一位劉元生先生——如果喜歡音樂的,應該知道他。他是香港管弦樂團的董事局主席,也組織了香港愛樂團,擔任主席兼團長。我到深圳三年前,即1980年,在廣州一個音樂會上,劉先生與廣州交響樂團合作,演出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我喜歡聽音樂,聽了他這個《梁祝》,興奮不已,就到後台找他去,表示我的欣賞,就這樣認識了,他還送我他灌錄的《梁祝》錄音磁帶。
我80年代在深圳創業,沒有熟人,也不懂得做生意,就想到他。他本身是個生意人。我們知道在國內,要做生意就做生意,做音樂就做音樂,當官員就當官員,不過劉先生這個業餘,可能比專業還聰明。他從小拉小提琴,30年前是香港交響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但自己本身沒有專門做音樂。我希望他指導我做生意,就這樣我們成了生意夥伴。
股份改造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股票。當時劉先生說了一句話:「我本來不想投資,但看到你想創業,我支持。」
公司改造成功後,其他三位股東,陸續把股票賣掉了。那時候萬科市值2,800萬,劉先生持有的股票,值400萬港幣。他一直沒有賣,到現在都沒有賣。當年的400萬,現在成了多少呢?現在是40億。所以有人說,劉先生是中國的巴菲特。當然我們現在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這兩年尤其今年,我發現香港和大陸關係比較緊張,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我想在這裏談談對香港的一些感受。
香港回歸,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專門到香港來,看到英國國旗下去,中國國旗起來。那時候陰雲密布的,我能感覺到香港人不確定的心情。英國人把香港視為東方的明珠,英國治下港人安居樂業,已經習慣了。當時很多香港人移民,劉先生也移民加拿大(後來許多人回流,是後話了)。香港那種複雜的心情,我們作為鄰居,來學習,來借鑒,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我們看到了關於遊客的各種行為。這裏我的經歷可以談談。上世紀80年代在香港,一次和劉先生幾個人搭出租車,我喝完可樂,窗戶一搖就扔出去,很習慣。當時司機就火了,恨不得車停了把你轟出去,場面就非常尷尬。我說我沒犯什麼錯呀,在大陸很正常的嘛。好在劉先生兩邊勸,沒有發生什麼衝突,司機沒有罷開,到地方就下了。當然我這個行為早就改了(眾笑),但是現在這麼蜂擁而來的大陸遊客中,肯定有這樣的人。再加上擁擠,再加上經濟形勢不大好,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我是很理解的。
大陸應借鑒香港 建立公民社會
香港有國際化的優勢,這優勢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如果深圳與香港聯手起來會怎麼樣呢?香港有個比較優勢,深圳的發展不是偶然,是學習、借鑒香港。
畢竟大陸改革開放了35年,大陸13億人,這一點香港應該好好準備。這方面,我覺得新加玻結合得非常、非常好,各方面優勢也發展得比較好。香港這方面我覺得還需要提高。
我還想說幾句話。香港現在確實競爭力在衰退,深圳,不是今年、就是明年 GDP 就超過香港。不過,就長遠競爭力而言,深圳有深圳的不足,比如大學教育的水平,與香港差距仍然非常、非常大。香港有很多優勢,中國大陸太浮躁,老是看誰的樓蓋的高,實在香港有很多很多值得借鑒。中國轉型當中,如何向效率型轉,向一個穩定的公民社會轉,香港很值得借鑒。今天藉這個機會說說我的心裏話:如果不向香港學習,香港沒有什麼損失,損失的是你自己。
再說中國環保組織阿拉善(SEE),2004年成立。深圳分會比較活躍,去保護紅樹林,指標是香港的米埔。米埔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成立、保護的濕地。雖然不大,卻在全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現在深圳的紅樹林90%已經毀掉了。如此下去,深圳就沒有紅樹林了。要保護這10%的紅樹林,指標還是香港。
我今天(2015年10月23日)上午在深圳,剛當選為深圳社會組織聯合會會長。深圳是一個改革開放的城市,NGO 在全國而言是走在前面的。深圳每一萬人有八個 NGO;國內其他城市,每一萬人還不到兩個。量度一個社會是否健康和穩定,是要看這個社會 NGO 的數量。你們香港呢?(有觀眾舉手)10個?還有沒有人要嘗試?我告訴你們,每一萬人有26個,應該是亞洲最高。深圳在國內遠遠走在前面,和香港比,差一截呢。


(二)
登山啟發 關注氣候變化
我是2002年登的非洲的乞力馬札羅(Kilimanjaro)。那一年我已決定要登世上七大洲最高峰。那次攀登的經歷給我一個轉變。我讀海明威1936年的小說,提到山峰有雪,就奇怪非洲的山怎麼會有雪?其實很簡單,就是很高嘛(眾笑)。它本來是一座一年四季白雪覆蓋的山峰。但我去了,峰頂也並沒有雪。為什麼?也很簡單,氣候變化。那我就來問,我、我的企業、中國和這個氣候變化有什麼關係?一查,關係非常明顯,就是碳排放、森林大量砍伐。
我是發展商,大量用水泥、木材,但我發現很多木材,都是非法從熱帶雨林砍伐而來。熱帶雨林的木材,70%運來中國,當中又有70%用到建築工地。建築工地中,70%是住宅。萬科是中國最大的住宅開發商,肯定和(氣候變暖)有關係。
那我怎麼辦?我就找上綠色和平組織。那時組織的北京幹事是香港 guy。不是 gay,guy(眾笑)。這個香港人是盧思騁,我一見面就表露身分。他知道萬科,也知道我,就很驚訝,說你來找我幹什麼?大陸的每一個大企業都躲我們呢。我就把我登乞力馬札羅的感受告訴他,我說我知道就算我不來找你,有一天你也會來找我,那不如我自己來找你。
他一聽很開心。我問他怎麼辦?他說,我們組織不負責怎麼辦,反正你環境破壞,我就打你,你怎麼解決,我們不負責。(眾笑)他就把我介紹給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讓他們來跟萬科聯繫,探討如何減少木材使用、保護熱帶雨林。
中國從2007年開始制定美國綠色建築標準。2009年的綠色三星環保項目,百分之百是萬科的,給一下掌聲。(眾鼓掌)
(笑)其實當年只批了一個項目,只有萬科一個項目。到了2010年,就有許多企業達標申請,萬科的項目佔比減少到了50%。到去年(2014年),我們佔38%。
萬科的市場份額是多少呢?2.5%。也就是說,市場上綠色三星項目的佔比,萬科最多只有2.5%。所以萬科不只自己做,也在市場上、在行業協會去推廣。比如說我們有個行業協會叫中城聯盟,有60家開發商。現在75%的綠色項目,是中城聯盟開發的,包括萬科佔的38%。我們是這樣走出一條綠色環保之路。
登珠峰險死還生
那我談談第一次登珠峰像到了天堂的那種感覺。當時離到頂峰,還有200至300米,按理20分鐘可以走到,我突然走不動。因為當時的氧氣走得太慢就不夠用,我的嚮導回頭一看,說王先生你沒有氧氣——難怪我肺快炸了,走不動。嚮導就把我的情況報告山下的總指揮。總指揮下令撤。不過實際上那個時候,下撤也很危險,繼續登頂也危險,那我就上去再說。
到頂峰了,實在沒氧氣了,就做兩件事。第一件是展旗,第二件是「取證」,就是拍照。一張可以 PS 嘛(用 PhotoShop 等軟件改圖,編按)。要360度環拍,證明自己上去了。那你想了,這個時間下來,差不多30分鐘,就趕快撤了。
有人問我登頂有什麼想法,我能有什麼想法?沒想法。要是有個想法,就是我能活着回去,我再登珠峰的話,我不是人。(眾笑)——到了峰頂,人都糊里糊塗,不是雪就是風,哪有什麼豪邁氣概?(再笑)全沒有。
下撤了,當時總指揮焦急了,他說:「王總,在8,700米的位置上,我們放了兩瓶氧氣,只要你撤到那個位置上,沒問題的。」那你怎麼拚死都會拚到那個位置上呀!
——到的時候啥都沒發現。(眾大笑)那時我走的狀態開始發生變化。我走着走着就發現,突然後腦勺很溫暖,好像溫煦的陽光照你的感覺,溫暖着就到了前面、臉頰上、到全身,感覺美滋滋的。感覺上只要你坐下來,閉上眼睛,你一定是很美妙的……很美妙。你真的是不想張開眼睛,如果有天堂的感覺,那就是天堂的感覺。
當然還是有聲音提醒你說:很美妙呀,但是你要選擇,是生活在不太美妙的世界上呢,還是要去美妙的世界。當時我還是清醒的,寧願待在這個不太美妙的現實生活當中。我沒有停步。不是不掙扎的,真的是很舒服。這個時間持續了20多分鐘,後來感覺又是風又是雪,又是很難受又是呼吸困難。沒氧氣嘛。
我那個嚮導還是很老練的。實際到8,000米以上,就會見到兩樣東西,一樣是空的氧氣瓶,一樣是遇難的登山者。嚮導見到空的氧氣瓶就撿,掂着有氧氣就給我換上。就這樣一路撿氧氣瓶,到8,600米上,撿到了一罐,還有三分之一,就給我換上。
8,000米上看見的遇難者,面部表情都非常安祥,甚至把手套、帽子擲掉。實際上登珠峰讓我感到死亡並不恐怖。第一次登珠峰是從北坡上去,這是2003年。
(封面:灼見名家傳媒;插圖:香港科技大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