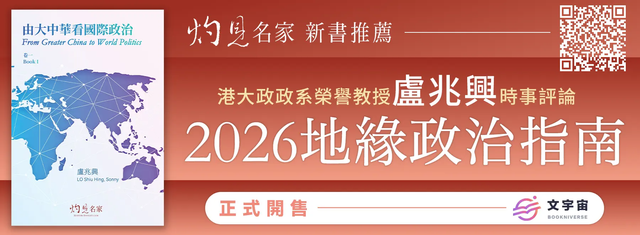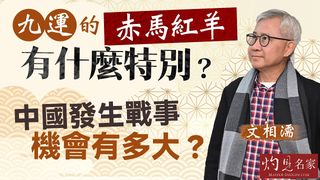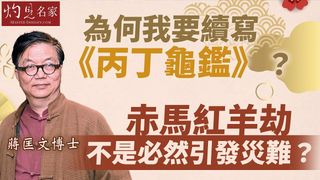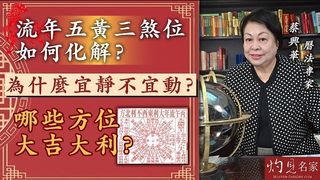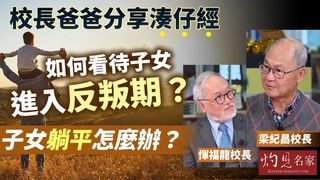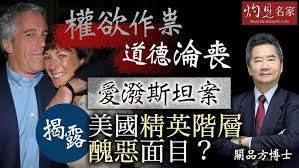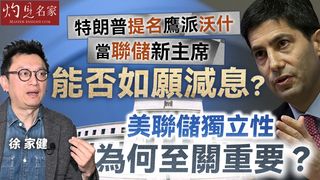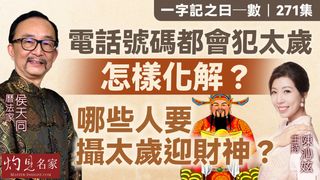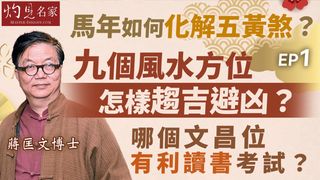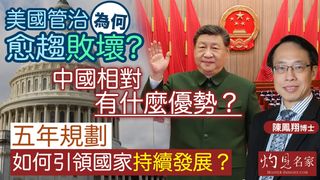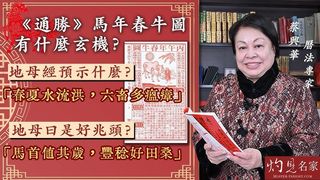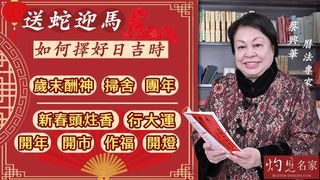上篇文章,葉劉淑儀講到香港當前困局的頭三個成因,在此部分,她繼續對數個更具體的問題發表評論。
(承上文)
另有一件事衝擊香港經濟,就是民主急劇發展。香港的民主,其實發展得很快。功能組別由港英政府發明,他們都認為推動民主,應該循序漸進,先要確保工商界、專業界別有代表,能夠貢獻香港經濟。選舉愈來愈多,影響政府效率,也嚴重衝擊政治文化。正如我進場前,有記者訪問我鉛水問題,很多議員都會問誰要問責、誰要人頭落地,問責風氣瀰漫社會。
選舉議題針對政府 公務員士氣下滑
就以鉛水來說,我認為首要保障巿民健康,找出問題源頭,完善驗水、驗血的方式,消除不必要恐慌,再去追究責任。追究責任可能很複雜,特首已委任法官領導的調查委任會,我們應讓他們負責。然而每次選舉,候選人都要尋找議題。尋找議題,當然是找政府的毛病,這就打擊政府與公務員的士氣。尤其近年政府推行問責制,這個政治任命制度能否與公務員磨合呢?許多無政府經驗、公營機構經驗的人獲得委任,但他們能否為政府提供專業知識或市場經驗呢?我們還未看見顯著成效。
當然,我們仍有一大問題,就是之前提及香港發展的兩大障礙:土地與人才短缺。除了住屋,各項發展都需要土地,例如貨櫃場、骨灰龕位、藝術中心、紅酒拍賣中心等。昨天就有藝術工作者說:「若要發展藝術中心,展品根本不知存放何處。一個儲存的地方都沒有。」物流業倉庫不足,貨櫃司機沒有拖頭擺放之處,各行各業都缺乏土地。
薪金追不上樓價 年輕人不滿
我們亦需要解決人才問題。高層次地看,我們要有全球性的跨國公司。按巿場經濟運作,公司生意足夠、業務廣泛,就付得起世界標準的薪金。比如全球性顧問公司與投資銀行,大學畢業生起薪點可達70,000元。本地律師行聘用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為20,000多,國際律師行則達40,000,通過試用期後可達80,000。在會計師行實習,收入約10,000多。過往調到內地工作,薪金很快升至幾萬。然而,現在內地需求減少,會計師也在煩惱薪金升幅放緩。公務員職位則十分搶手,不但起薪點高,還提供大機構獨有的晉升階梯,福利又好。
我1972年在新法書院教書,薪金為1,400元,現在相同職位,薪金約為13,000元。試想40年內升了10倍,但與房價比較,又如何呢?建築師跟我說,1967年美孚新邨初推出時,500呎的單位只售22,000元,1972年升至40,000元,今天更已升至600萬,40年內升了120倍——而工資只升了10倍。所以,去年佔領中環行動,年輕人抗議要求社會公義,並不是沒有道理。他們覺得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背後源於這個問題:工資趕不上房價,看不到前路、看不到何時能夠成家立室。所以,佔中之所以發生,是出於回歸十多年來管治有缺失,社會、經濟、民生發展都停滯不前,不是純粹因為普選。
土地短缺
以上點出不少問題,現在讓我提出對策。第一,我認為政府要解決土地短缺、缺乏熟地的問題。政府提出很多發展新市鎮的計劃,如新界東北、古洞北與粉嶺北,便是梁振英上台後提出,最近終於通過城規會。這次發展計劃,城規會收到了近50,000個反對意見,開了45天會議才悉數處理完畢。特首上任近三年,才就計劃刊憲收地。有官員告知,不論粉嶺北、洪水橋、東涌東,各類發展計劃可以提供土地,都要在十年後。此外,還有發展局提出的岩洞和填海計劃。其中一個較為人熟知的擬建人工島,位於港島與南丫島附近,但我認為這會引來更多爭議,例如環保人士反對,何況還要建橋鋪路,30年後才能完工。完工後如何訂定呎價呢?2012年,發展局長表示政府有150公頃熟地,傳媒指出有誇大成分。其實即使沒有跨大,一公頃也只等於一個標準足球場。現在熟地不多,且分散香港各地。土地缺乏,是香港一大管治困境。
須正視基層勞工不足 畢業生競爭激烈
第二,要解決勞工不足問題。很多基層行業都難以聘請,如的士司機、保姆車司機、校車、酒樓、建築,然而輸入外勞卻很困難,連港鐵公司都只能輸入50個。過往興建機場時,有個「補充勞工計劃」,輸入必需的建築工人。今時今日,畢業生尋找高薪職位,要面對全球競爭。他們的學歷、技術,能否勝過全球人才呢?
政府運作有待改善
土地、人才以外,還有政府運作模式。最近世界經濟論壇,將香港評為全世界效率第四高的政府。這點可喜可賀,我亦相信政府名副其實;政府官僚架構的運作,維持一定效率、誠信、可靠程度。然而世界急劇轉變,我們的政府做事卻不擅前瞻、開創,做事缺乏時代感。政府雖然很努力,比如規劃啟德,比如希望成為智慧型城市,但外國對於智慧型城市的規劃,比我們先進,似乎我們政府有很多技術,仍未掌握到。再加上四年一次的選舉,政黨政治的誕生,各方面衝擊,難免損客政府運作。政府有時顯得因循,比如規劃太慢,居民遷出十多年的土地仍未能發展,也無法給巿民清晰願景,巿民自然對政府沒有信心。
所以我認為,政府要打破目前管治的困局,既要解決土地問題,培養更多尖端人才,也要改變運作模式——即掌握世界潮流,政策勇於開創、富時代感,措施能夠有突破。比如退休保障,張局長十多年來,一直只說「三大支柱」,即自身儲蓄、強積金和政府福利,沒有新思維。以舊思維、舊理論強撐十多年,趕不上時代發展。以上我分享數端,我認為目前問題之所在,及一些回應方法。
問答部分節錄(註)
問:葉太,你剛才提過香港土地和人才的問題,但你沒有提到信任的問題。香港對公務員體制的信任問題會不會是不同的事件而慢慢減弱?你又如何看中港的關係?
答:信任問題,如果你聽曾鈺成說,很多人說有普選有票有信任,可見民意授權是代表某程度的信任。但以官員來說,誠信廉潔是非常重要的。香港回歸將近20年,我覺得一國兩制大致上運作是好的,很多在內地沒可能發生的事都在香港發生了,例如法輪功在行政會議門口的抗議,中聯辦門口的抗議,不同政見的,甚至針對內地的團體的言論自由在香港完全沒有問題。
一國兩制大致上很成功,但我同意曾鈺成有一次在港大畢業同學會晚餐中所說的話,他覺得港人治港不盡人意,不太理想,包括我們公務員行業出身的人,例如有觀眾提到的湯顯明,其實我個人認為他沒有甚麼大罪,到目前我看不到他有甚麼大貪。但你提及的是文化,那種酬酢、貪小便宜的文化,當然較令人震驚的是我的舊同事許仕仁的案件,或者是立法會都查過的高官幫地產商工作,這些都影響了市民對管治班子的信心,所以我們需要強化廉政誠信。
其次,你問我對中港關係,中央政府和香港的關係的看法,這是香港管制上要處理的一個很大的問題的挑戰,很多人說中央政府干預香港,其實並不是,他們是要跟香港保持聯絡,比如跟議員聯絡是要幫特區政府,這是因為特區政府受到很多衝擊。老實說,特區政府是比較弱勢的,所以中央政府要間歇性地支持特區政府,職責上支持香港。
的確內地的制度跟我們的不一樣,我們受到一國兩制的保障,司法獨立,我們用普通法,他們用大陸法,兩者文化上有很大的分別,做事上也很不同。內地是一個很龐大的文化系統,它有自己幾千年做事方法,不是純粹泛民批評內地專制,獨裁那麼簡單,如果有看過Samuel Huntington的名著《文明的衝突》,書中明顯地指出世界七大文明之一中華,是一個很獨立,獨特的文化,有自己的思維和做事方法,有它自己多年思想的習慣文化,處理問題的方法跟別人不同。
但香港亦因為是百多年的殖民地,受到西方文化很深的影響,所以,在文化方面有很多東西跟內地格格不入。這個是兩地的不同之處,我覺得兩地是應該互相包容的,不應該指責對方是落後的文化,我們才是先進的文化。
我舉個例子,內地官場的文化是怎樣的呢?內地的官場文化是內地的人才要冒起,西方的政治人才要冒起是靠選舉,要宣傳自己、出位,要有鮮明的形象才能勝出。但內地的文化幾千年都是一樣的,沉潛隱隱,要很沉着和收藏自己,到真正的決定時刻才表露自己的真正想法,按部就班,根據自己在制度裏的地位做自己應該做的事,不像西方的政治領袖年年公開自己參選總統,參與節目。內地的人才的文化是不同的,中國培育人才上位的方法跟西方是很不同的。雖然有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但相方可以互相借鏡學習,或者我們民選政治人要學內地官員,適當時候要忍耐,內地也要學習西方的透明度,所以西方經常批評中國。
即使西方對中國有很多的批評,他們沒有對主席夫人做出任何負面評價,反而覺得中國很不一樣,因為中國有一個現代的領袖和亮麗的第一夫人,有個性。所以,西方要求的領袖就是需要有個性,但中國的領袖就是隱藏自己直到上位,這是中國文化累積幾千年而引致的不同,我們應該互相包容,互相學習,而不是像有些香港人覺得我們擁有的是先進文化,不應該被低等文化統治。不同的國家有其特徵,而這個正所謂 “mediat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的責任是特首的責任。
整理:朱淑滎
(註:部分問答內容參考新民黨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