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方以貿易保護為由打壓中國貿易發展,然而現今中國不一定處於弱勢,「商戰」上如何應對將會大大影響中美兩國關係。

美國也一直擔心其他民族和文明的崛起,一些人憂慮白種人文明最終會被他們所視為的劣等民族文明所征服,甚至所取代。今天隨着中國的崛起,他們開始擔憂中國文明會威脅到西方文明。

兩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迎面相撞實為必然。美國既沒有能力和辦法來改變中國,也沒有能力和辦法來圍堵中國,未來的中美關係可能呈現出一個世界、兩種體系的局面,即存在著兩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

在美國看來,華為等中國公司產品進入的網絡空間愈大,表明美國所佔份額的減少;華為所佔網絡空間愈大,美國所能收集到的信息就愈小。

因為全球化狀態下各國之間的互相依賴或者關聯,一個國家自私的考量就會對其他國家造成更嚴重負面的影響。這些年美國單邊發動的貿易戰就是明顯的例子。

所有經驗都表明,成功取決於創新,即以自己文化為主體的創新。也就是說,照抄照搬外國經驗不行,固守傳統也不行。從這個角度來說,今天人們提倡文化自信不可以是復古,更不是庸俗文化的回歸。

很多民主的理想和為實現這些理想而設計的制度很難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實踐層面,民主演變成分化政治,或者說,民主政治變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五四運動的主題是民主和科學。民主是開放政治,與傳統封閉政治相對;科學是理性,與傳統的迷信相對。為了一些政治原因而否定五四運動,並無道理。從文明演進的角度來看,五四運動的大部分是做對的。

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應當是一帶一路的初心。把一帶一路做得更有效率、更好和更可持續,也是今天中國所考量的問題。

美國在海洋上仍然是不可挑戰的霸權,在金融和互聯網上儘管美國保持領先,但也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壓力。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竭力打壓中國的知識經濟和技術並不難理解。

中國可以根據西方提出來的問題,反思如何把新疆和大西北治理得更好。在新疆和大西北,必須把發展和反恐區別開來。對恐怖分子和需要工作培訓的這兩類人,絕對不可混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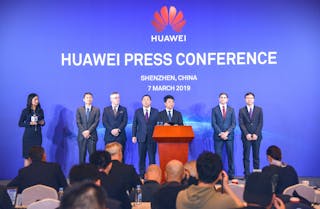
政府的「幫助之手」是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東亞的「發展型政府」尤其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政府的「幫助之手」發揮到了極致。

中國監管問題的起源具有特殊性,那就是存在着一種可以稱之為「制度隔離」的現象,即監管者和普通人民並不在同一個制度體系裏面,或者他們表面同處一個制度體系,但被一種制度所隔離。

對中國來說,不開放導致「挨打」和失敗,這是大歷史的教訓。所以,中國不會走回頭路。近年來,即使西方盛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也一直堅持繼續的開放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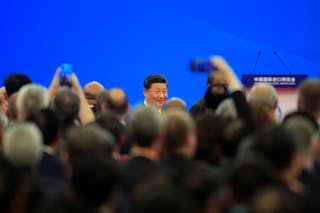
一帶一路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而正如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所顯示的,基礎實施建設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經濟發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在房地產領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三大既得利益,沒有一屆政府有能力同時應付這三大既得利益。要理順房市和股市兩市,就要掌控錢的流向,即把資金從房市導向股市。

資本主義的成功在於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但現在中產階層面臨幾個方面的夾擊,有來自技術的、有來自資本的、有來自社會的。「憤怒」是今天西方中產階層的主要特徵。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權。但獨霸產生其自身的危機感,即總是會感到自己的霸權地位要被他國所取代。

今天中國的海洋戰略也迎合了中國作為商貿國家的需要,而傳統的陸地國家心態仍然影響着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關系。在向海洋發展過程中,一旦遇到瓶頸,就很容易轉向陸地。

美國學者傅高義教授1979年出版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引起廣泛關注。鄭永年指出,日本的發展經驗也值得中國借鑒。

如何應付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呢?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有,但從來沒有成功過。原因很簡單,沒有任何社會力量可以和資本進行有意義的競爭或鬥爭。

中國企業家群體表現出至少如下特徵:離錢太近,離科學技術太遠。大多數人見錢眼開,唯利是圖,但對科學技術不那麼感興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業家更多的是近代工業化的產物。

亞洲「主動」的思想殖民階段。通過亞洲各國的反殖民運動,物質意義上的殖民地消失了,但思想上的殖民地主義根深蒂固,不僅無意識地存在下來,而且變本加厲。

政府須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更須賦權社會本身培養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使得社會有能力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靠政府平衡。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什麼?儘管表面上看是實足的貿易戰,但實際上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和衝突。這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具有文明性,是中西方文明演化的產物。

儘管中央政府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來調整分權和集權,但分權和集權之間需要相對穩定的邊界,沒有邊界,政策執行者就會無所適從。

歷史是弔詭的。革命畢竟經常在發生,所以人們可以說托克維爾陷阱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但同時,至少東亞發展模式也表明了,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

即使在微觀領域,新一波以黨領政的改革也出現了黨的機構迅速擴張的情況。例如在企業界和社會組織,人們往往把黨的領導,簡單地理解為在每一個企業和社會組織設置黨的機構。

十八大以來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反腐敗與預防腐敗,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正式成立的監察委,成為平行於執行機構的獨立機構。不過,在整治腐敗和亂作為之後,現在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不作為」。

一帶一路的國企投資往往被誤認為中國的國家行為,而非企業行為。對一些國家來說,它們難以把國家和國有企業區分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