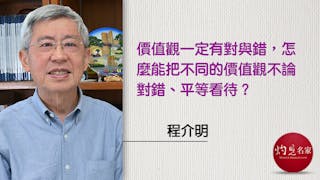
什麼有價值?什麼沒有價值?而價值觀的表現,不在「有」與「沒有」,「1」與「0」之間,而是價值的比較。

古代漢語和粵語一樣,「揚」作「宣揚」解時,是可以自由運用的。

何文匯教授與觀眾分享他個人學習中文的體會和心得,提出要精通中文,除了多讀多寫,還要學會分辨平仄、懂得運用反切尋找正確讀音、了解近體詩格律,並藉此深入認識中國語文、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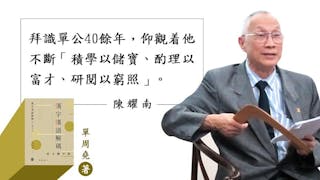
拜識單公後,就常常想像:好學而早慧的他,發覺自己姓氏與常字異讀,也在他豐沃的心田,早就播下千百種子。

若我們口頭上的「唔多」是古語之遺的話,古代文獻當有寫作「不多」,而義為「不大」的表達方式。

晉 葛洪《抱朴子.博喻》已有云:「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這是勸那些身居高位者,用人時要注意用人的長處,不要偏愛「gɐt2」(責難)人的短處。

我們實在不當妄自菲薄,視自己的母語為非雅語,進而拚命拿普通話詞彙來取代自己的母語詞彙。

孔夫子有教無類,來者不拒,所以他的學生什麼人都有;無怪乎當時人也有認為孔門很「雜」。

近日筆者在一些電視劇集裏面不止一次聽見藝員的對白看到「初來報道」四字。筆者真的覺得很奇怪。

說到「十」這個字的寫法時,粵語會說是「一劃一㢥」,也就是「一橫一豎」。

中國歷史和文化淵遠流長,語言和文學有很優雅精緻的一面,但人的心理和行為卻有很殘暴血腥的一面。

粵語「得意」是「可愛」、「有趣」的意思。其實「得意」當是「得人意」的省略。「得人意」即「合人心意」,「得人喜愛」的意思。

「揭」有2000多年的歷史,「屙」和「定」都有過千年的歷史。粵語之雅,於此可見一斑。我們對自己的母語有多大的誤會,於此亦可見一斑!

孔子的思想是偉大的,是實用的,並不迂腐。腐儒不善用孔子的學說,使它腐朽了;獨裁者歪曲孔子的學說,作為欺壓人民的工具,把孔子的思想敗壞了。

筆者小時又聽過某廣告,裏面有「痕癢」一詞,於是一直以為粵語的義為「癢」的「痕」,若要在語體文中表達,就可以用「痕癢」這個詞。到了執教鞭之後才知道原來現代漢語共同語當中根本沒有「痕癢」一詞。

「不要碰我的東西!」這個詞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作「玷」。其實「玷」只有「污點」和「玷污」的意思,重點在「污」,而非「觸碰」。

中文的文化訊息比所有拼音文字都更豐富、更濃縮。同樣內容的書籍,中文版最薄、佔用空間最小,閱讀起來,中文版所花的時間最短。

在粵語裏,「個」這個量詞,有一些比較特別用法,其中一個是︰可以用於定語和名詞之間,表示領屬。如「我個頭」就是「我的頭」。

老曹一生都奉獻給了《大公報》,一張旗幟鮮明的愛國報紙。他一生磊落光明、待人誠懇,不斷追求知識,克盡報人責任,樂於提攜後輩,大公人不會忘記他。

老曹等前輩經常教導我們,處理新聞,要有自己見解和看法,如果人云亦云,那是很難有競爭力的。

明周夢暘《常談考誤·長音仗》:「長字三音:平聲在陽韻,上聲在養韻;平上二聲人多知之,去聲鮮有不誤者。」

《漢語大字典》云:「古籍中多作『沈』,今『沉』字通行。」

「同化,指兩個本來沒有意義關聯的詞,由於經常處於同一語言結構中,其中一詞受另一詞意義的影響,由於類化的作用,也產生了與另一詞相同或相近的意義。有人把它叫做『沾染』、『滲透』或『同步引申』……」

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三隻老鼠:一隻是《詩經·碩鼠》中的老鼠,一隻是秦始皇時期丞相李斯的老鼠,一隻是漢武帝時期酷吏張湯的老鼠。

本講座改為影片模式播放,可先下載閱讀資料。

《荀子‧大略》:「《易》之〈咸〉,見夫婦。」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曰:「山北水南,日所不及。」日所不及,故幽暗也。

文化是要傳承的,但是有系統的文化傳承,主要靠語言文字。如新加坡把一門外語(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結果以前南洋一帶多語的環境,在新加坡逐漸消失,方言裏面豐富的文化內涵,也隨之而消失。

「亢,過也」,粵人所謂「過龍」,就是「亢龍」。

周邦彥《六醜·落花》說:「春歸如過翼」,其逝也速,宋人遂以「春」為「一日夫」(見《太平廣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