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有研究和分析指,如把建立無形資產的費用重新計算,以資產的形式入帳,那麼,這套較能反映無形投資的資產負債表,其實更可以解釋資產價格的變動,更有助投資者和企業作分析和決定。

從不少的數據庫,我們在彈指之間就能找到「加法」的交易數據,如A公司宣布收購B公司,但要找到「減法」的數據集,如C公司處置子公司D,卻不是垂手可得。這還不只,減法的數據,很容易被加法的數據所遮蓋。

大多數的職業經理人骨子裏是希望擴大業務版圖,而不是縮減業務,此無他,餅乾大小和報酬多少是直接掛鈎的,而報酬的數量級,又以認股權證為大頭,現金工資為零頭。 而對權證最敏感的,多數是併購時的刺激。

金融投資與產業投資有重疊的地方,也有不可照版煮碗的地方。競爭的環境不一樣,昔日的汗馬將士,不一定能適應新的戰事,改弦易轍,其實也是恆常態的一種。

有併購出身的職業經理人的收購型企業,最能挖掘具有協同效應的收購机會、最能識別被購企業的潛質、最能以「較」低或合理的價錢買到心頭好。所以他們作為併購型企業的總舵主,至少履歷上是沒有錯配的。

最合適做公司一把手的,是由熟識收購合併、對投資項目有高敏感度的併購專家;反而,由紅褲子出身、在企業內由低做起的産品專家、天才程式員、營銷能手、財會掌櫃等,不一定最能勝任今日着重外延拓展的企業新常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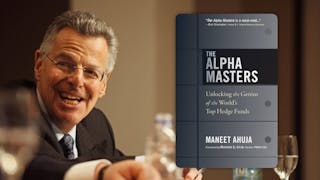
諾貝爾經濟學人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早前來港,現借此分享教授早前為一本關於9位知名對沖基金的著作所寫的後記(Afterword)。

隨着創業投資日漸普及,機構投資者近來將BSM期權模型,應用為「實物期權模型」,找尋新的視角和工具。

孫正義在是役中對美國矽谷中人大有功勞才對,可是,同行始終如敵國,在事後的各種表述之中,矽谷中人對孫公的作風的批評,愈加尖銳。

儘管願景基金的大膽策略在矽谷面臨挑戰和非議,仍然有不少國際投資者相信其願景,並願意支持它投資於使用新興技術來破壞傳統行業的公司身上,而行業的定義可能包括創投業。

孫正義一向被矽谷中人和華爾街描述成只懂得撒錢,但在這最賺錢的一票中,卻現了一手砍價的談判技巧。也許很少人真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能耐,但這幾下過招,如果純粹用銀紙論輸贏的話,掌聲的方向理應相當明確。

矽谷一個重大的缺點,那就是排外,尤其是對非白人、非男性、非哈史等大院校的外來人,哪怕你手上有錢、有業績。

上周將莫言先生的一篇舊文新讀,今周再就手上兩篇中外對大江的訃文,比較其異同,體會一下大江先生如何感染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讀者。

莫言借魯迅先生的説話,指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不是「書生」躲進小樓,寫出「自得其樂」的「風花雪月式的文學」作品,而是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性関懷」,有「嫉惡如仇」的「靈魂」!

獨角獸令投資者驚艷,尤其是對為數不少在它們成長晚期才湧現的金融投資者,尤具吸引力。這些投資新貴過客,放大了優先清算權的使用,又熱衷於把獨角獸作為追加投資的載體,使獨角獸在茁壯過程中,顯得人細鬼大。

獨角獸之所以令人興奮,因為它有許多未被開發的潛力、有讓設資人想像的空間,而假想的其中的一個維度,就是它們雖然羽毛未豐,但卻有作為收購合併的載體的潛能。

由於大量背景不同的單位投資獨角獸,那所謂的中、晚階段創投,或稱上市前的融資輪,成為眾矢之的,而當中又與金融投資者引入的優先清算權和「孫公司投資模式」最為惹火。

巨浪翻騰之下,原來有不少的創投老手,卻一早就不住地提醒大家,錢多其實會令初創企業,迷失初心,墜入黑洞。

創投家有時會高談自己做創投的決策過程,是本能驅動,不是科學──即使是投資於科技科學的一門生意,歷來在決策的過程之中,原來也很有「反科學」的一面。

原來谷歌的上市,也還有對創投打臉的一面,其成長由天使至上市,都表現着對當時(至今)「傳統」型創投的一種年輕人的叛逆。

美国矽谷的創業投資作為一個生態系統,有兩個大流派。如果前面的一派是自由派,第二派就是實務派,他們實施財務控制,頭腦清醒,有接地氣,是現實主義者。

美國西岸的矽谷之所以在上世紀70、80年代,打敗如日本的芯片工業群和美國東岸波士頓的資本創投群,與矽谷風投界的人與人,跟公司與公司之間一種獨特的弱連結有關。

收購合併是企業外延發展或起死重生的手段,千禧年初由於大數據開始普及,憑藉多組數據庫和統計程式,提出了嬴家詛咒的説法。只是,當局者和旁觀者各有各忙,似未有同識。

追源遡古,美國的併購業或可從19世紀的約翰.摩根在銀行業、鋼鐵業和鐵路業的合縱連橫始,一浪接一浪,到2020年代,起碼有6、7次的潮漲潮退。

這株夾縫中的小花,盛放時是艶麗的洋紫荊,風雨交加時就是荊棘滿途。然而,風中勁草的生命力,在雨過天青後的艶陽天,自能一展英姿。

由民間舉辦的商務會議,如能及早在香港復辦,對本港、大灣區以至內地,都會有很大的輻射作用的。

關於星港雙龍爭輝之説,多以狄更斯的《雙城記》來比喻;但不才卻想以港式俚語「代客泊車」來形容。

人始終是人,在生活行事上有許多的習慣和系統的局限,讓光陰不斷地從手指罅隙或瑣碎夾縫中枉然流逝。

資產的一買一賣才是股權投資人的技能和專業職稱,持有期當中的附加值當然也很重要,但每當當事人成為當局者後,就經常會有角色混淆,墮入外行人管內行人的誤區。

金融資本主義成為西方社會建造全球化時的尚方寶劍,當全球化浪潮,席捲亞洲大大小小的經濟體時,起先的確是措手不及,但在長視角之下,亞洲諸國是否輸家?金融大鱷是否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