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18年,香港管治有如衛生黑點的後巷,藏污納垢,無法洗滌,港人怎能不感到悲哀?

政府宣傳中有一個常見詞:齊心抗疫。每當見到這幾個字時,我覺得啼笑皆非。官員沒有同理心,對市民的苦況冷漠抽離,政策和言行經常都是「堅離地」。既然政府不與市民同理,市民又怎會和政府齊心呢?

香港的普通死物如有破壞,政府官員反應大而快。文物受破壞,官員反應較遲鈍,但相信他們還會做補救工作,因為這可以成為功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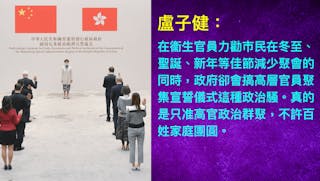
林鄭喜歡説,抗疫只涉及科學,不涉及政治。這種說法除了是妄圖佔領道德高地的虛偽外,根本就是錯誤。能否成功抗疫,就是當前香港最大的政治。

「夫復何言」和「痛心疾首」這兩句説話完全適用於近日有線電視新聞部的崩壞。這場崩壞早有先兆,換股東,換新聞部管理層,都是為了現在的情況作鋪排。

本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香港疫情控制的情況比新加坡更好,這是因為香港市民警覺性更強,很快已經做好戴口罩、勤洗手的衛生措施。何以後來香港情況好像比台灣、新加坡等地差呢?

馬雲崛起與生存之道,唯靠創意。在國進民退、黨領導一切、一切權力歸中央的大格局下,他是否仍能適者生存,對香港人也有參考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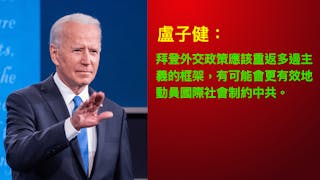
特朗普以「美國第一」的意識形態確立了對華鬥爭的戰略理據。拜登未必有像特朗普做大動作的能耐,但由於對華政策重新定位已經基本完成,他蕭規曹隨並不太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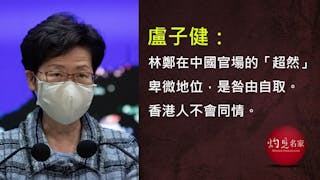
林鄭月娥弄到香港特首的地位在今天中國官場中如此「超然」的卑微,是她咎由自取。

今天香港,不少人要在維護公義和配合政權暴政之間作出選擇。香港崩壞的速度有多快,視乎有多少人勇於維護公義,抵制暴政。

香港正值多事之秋,政權打壓醫護未必得到應有的關注。但如果醫護真的被鎮壓,香港將遭受重大傷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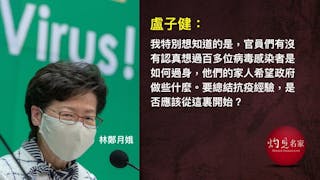
第三波疫情為香港帶來極大的傷害,也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應當首先在過去大半年的抗疫經驗中探索,應該依賴付出了大量心力抗疫的市民的智慧。

在這場有關三權分立的爭論中,香港有很多學者、法律界人士、評論員很認真地討論什麼是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相互關係等等,但沒有觸及兩個核心問題,亦因此只能與中共官員各説各話。

以打擊苦主洗白警隊在7‧21事件中的表現,與浪費資源的全民檢測大龍鳯看似是兩件沒有關係的事,其實是有一條紅線聯繫。

創辦人被捕,傳媒大樓被200警搜查,壹傳媒股價卻不跌反升。市民以買「自由股」來作為抗爭手段,成為國際新聞。

中共好幾代領導人,都明智地利用香港的國際地位為國家增值。但今天北京卻好像視這種地位為毒瘤,去之而後快。

過去德國都與美國保持距離,香港問題導致了突破。德國作為歐洲的龍頭,其取態有可能影響其他歐洲國家,為中國外交帶來更多壓力。

7月19日,特區政府發表聲明,指豁免檢疫安排有其實際必要。聲明充分展示特區政府抗疫失誤的兩大關鍵因素:政治掛帥,永不認錯。

抗爭的目的是維護市民的利益,抗爭運動不能滿足於60萬人或者170萬人的支持,而是應該嘗試爭取所有香港人。

香港本來是內政問題,社會動盪是因為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加上香港人抗拒北京過度介入香港事務所引起。可惜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管治的失敗。

《港區國安法》不單只是涉及國家安全,也不單只是一條法例。國安法是對港政策的重大舉措,為北京全面管治香港清除制約。

無能也罷了。既然港人討厭,北京又不信任,無能的林鄭政府早應引咎辭職。不辭職也罷了,好心他們也作些少謙卑狀,把尾巴夾在後腿之間,不要再扮信心滿滿、頤指氣使。禮義廉的港官,知不知道恥字怎麼寫?

去年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本來是非常和平。如果不是因為遊行未完政府已經發聲明表示會如期把逃犯條例修訂提交立法會通過,就未必會有當晚的警民衝突,就未必會有「6.12」民眾包圍立法會的一幕。

2020年6月,香港。在國安法的巨大陰影下,將來叫「結束一黨專政」是否違法,特區官員只能含糊迴避。六四維園集會被禁止,從此消失並不為奇。香港抗爭運動會否像內地八九民運一樣,將會面對漫長的寒冬?

國安法的論述是「文攻」,意圖令中立甚至淺黃的市民離棄抗爭運動。至於國安法本身則是「武嚇」,主要作用是震懾「和理非」,促使他們與前線和勇武分化。

北京以為加強干預能夠鞏固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但愈干預,政府愈不得人心。於是把國家安全這個稻草人搬出來,汚蔑香港抗爭運動是外國干預所推動。

如果我們認真分析監警會的意見調查結果,結論只有一個:警隊不整頓、香港沒出路。

平情而論,政府向市民派口罩,就算不是大好事,也不應該是什麼壞事,何解會有這麼多的批評?

我們要在抗爭中堅持生活。唯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打贏這場持久戰。

什麼時候中聯辦一個辦事機構變成一個權力機構?什麼時候中聯辦主任一個部級官員變成有權監督「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