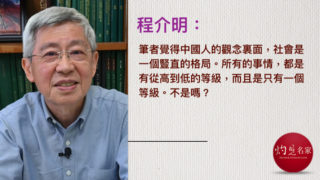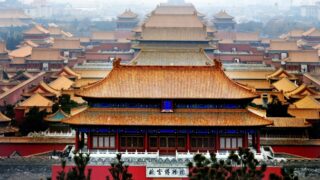我們常說,中國是禮儀之邦。筆者這個「番書仔」的淺見,那是自孔子以來,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案。這種方案,需要把社會設想為一個縝密的結構格局,每一個人都在這個格局裏有一個特定的位置,所謂「各安其位」。然後要求或者期待每一個人按照自己的位置服從特定的規矩,即「安分守己」,嚴格要求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更重要的是,要每一個人發自內心去遵從這規矩。這是筆者理解的「禮」。
在這個格局裏面,於是有了非常嚴格的長幼、上下、尊卑、男女,因此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含姐妹)等的相互關係與禮儀。現在中國內地的大家庭愈來愈少,尤其「一孩政策」(1978年)的影響,兄弟姐妹的概念幾乎成為歷史;2015年提出雙胎政策(即父母都是獨生子女可以生兩胎),情況並沒有太大的扭轉;最近取消「一孩政策」以後,也沒有出現「搶生」的情況,看來新的一代不太願意生孩子。於是,每個人的兄弟姐妹,就趨向於「1」或「0」。隨着,叔、伯、姨、姑的概念也會愈來愈淡薄。
在香港,很多上一代,還有來自大家庭。一到春節拜年,一家團聚,就會出現親戚之間稱呼的重溫──媽媽的舅舅的孫子,叫什麼?爺爺的姐夫的妹妹的兒子,又叫什麼?小學的時候,有一科《尺牘》,原意是教寫信的,就要學很多稱謂,包括各種輩分的稱謂。什麼「姑丈公」、「姨婆」,現在變成都是一年一度春節團圓才叫的。還有,同一個人,有些孩子叫她婆婆,為什麼另外一些孩子卻叫她嫲嫲;虧中國人的孩子從小就習慣了懂得這種差別。在他們的腦子裏,從小就有了輩分的概念。
不婚不生 家庭轉型
就算是香港,這種情形也正在式微。很多新一代的,不婚不生。生的,「一個起,兩個止」,對下一代來說,有了姑媽,就不會有舅父;有了叔伯,就不會有姨媽。也會絕少出現「三姨媽」、「六舅父」之類。
西方社會沒有這些「麻煩──“uncle”、“auntie”、“nephew”、“niece”、“cousin”加上“grandpa”、“grandma”,也就完了。不分男家、女家、父方、母方;在美國,有時候甚至直呼其名,不分老幼、尊卑。
輩分,在華人社會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這就不限於家族之內。機構、官場、學術界……都是如此。社會上是「敬老」,至今,在許多華人社會,被稱為「您老人家」、「您老」、「老先生」,是一種尊稱。不止一次,在內地講課前,主持人介紹說「程先生年事已高」,聽起來就不大舒服。大約30年前,初到美國,在酒會上稱讚對方老資格,旁人耳語,說這樣很不尊重。
一個機構裏面,坐在一起開會,主席當然是最高職位的董事長、總裁,往往不只是會議主持,還是主要發言人。主席沒有指示,下面(「下面」)不會主動發言。即使是下面發言,也有從高職位到低職位的排序潛規則。要是新進的年輕人,「搶先」發言,就會招致「白眼」,「你算老幾!」日本學生告知,老師在課上提問,要是班裏的「前輩」不回答,「後輩」不敢答——前輩,可以是籃球隊的隊長、合唱團的聲部長、學生會的幹事,等等。可見輩分在日本是深層的文化特徵。
學術輩分 刻意分等
在學術界也是這樣。在台灣,有些大學,近親繁殖是常態。系主任常有抱怨:「輩分高的不願意當主任,可系裏面的成員,都是我的老師輩…… 難呀!」多年前,香港一所大學,某系主任還規定系裏面的同事,發表論文,作者必須有他,而且必須他的名字排頭。師生之間,博士導師規定學生必須在他的(狹窄的)領域裏做研究,因此20、30名博士生,都做着幾乎是同一的題目,時有所聞。更有規定博士生只研究導師自己的學術思想的。筆者也遇到過剛來香港的博士生,說:「我沒有自己的題目,反正老師您叫我做什麼題目都可以」(!)。
會議拍照,那是內地開學術會議的「規定動作」。本來是時間非常緊湊的一個學術會議,拍一張集體照,還是非常重要的項目。拍照的時候,排隊是一個大學問。前排、後排、當中、靠邊,都很講究。若干年前,筆者當時是副教授,一次被邀作主旨報告,拍照時,有過百人,指揮者拿着擴音器喊道:「教授的在前面,不是教授的請站到後面」;筆者立刻識相溜到後排去。
很多年前,是世界銀行的項目。進到旅館,當地接待的,特地說:「我們給團長準備了最好的房間,是周總理住過的」,團長其實只是世行一位普通的研究員。第二位是美國的華人副教授,安排到一間大套房;筆者住小套房。而我們之中其實學術輩分最高的北大一位教授,則住進了一間普通標準間。接待者在分配的時候,還特意申明房間的等級。同一個團,順便訪問了一所大學,臨走,贈送紀念品,送給團長的,「這是本校一位全國知名的美術教授畫的。」美國華人教授,「這也是本校一位本省名家畫的。」輪到筆者與北大教授,「這也是本校不錯的教師作品。」是刻意作等級區別的。當時我們就議論:團長有特殊的紀念品,可以理解為給機構(世銀)代表的,那也常見,為什麼故意要把其他人劃分等級?現在再想起來,只能說中國是一個等級社會,所以一切禮儀,都是按等級安排的。
差距格局 文化特色
這些等級觀念,影響到改革。高等教育多次嘗試改革大學的職稱。最大的困難是大學職稱與公務員等級的掛鈎(有稱此為「官本位」制度)。比如說,北大、清華的校長,相當於副部級(副部長)。一般大學的副教授,相當於縣級(也是軍隊的團級)。這就還牽涉到工資、福利待遇、退休待遇、政治待遇(例如參加哪一級的會,閱哪一級的文件,也牽涉到人事調動的準則、調動資源的權力),等等。不過引入市場經濟以後,這些對應就逐漸淡化;尤其是對外接觸較多的地方,就逐漸不太嚴格。
筆者在港大當副校長的時候,到農村從事研究,就常常給了對方接待的困難。港大副校長,需要有副廳級的領導接待,如會見、宴請。有時候,到的是基層的農村,要找到相應級別的官員,就有困難。其實筆者只是以一名研究員的身份做項目而已,並不代表大學,更不帶行政身份。逼不得已,有時候就「瞞報」,以免對方難做。
這也聯繫到對於大學行政職務的看法。在香港,當系主任、院長、校長副校長,是一時的職責;任期滿了,又回到基層當一名學者。但是,在內地,到處都有人堅持稱筆者為「程校長」(注意:還略去了「副」)。人們往往認為當校長是「升級」,不當校長叫做「退下來」;終身總得按最高的職位稱呼。在台灣,早期也有類似情形,常常有「退下來」的軍人,繼續被稱為連長、團長。西方就很不一樣,筆者在倫敦大學的其中一位博士導師,中途轉到英聯邦事務處工作,就周知各人,以後不要稱他為教授。近年,在中國內地,也逐漸有了轉變,當一屆院系的黨委書記,又回到基層從事學術工作,已是常態。這是文化的轉型。
所以費孝通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差距格局」(筆者譯為Hierarchical Configuration),是非常準確的概括。只要看看,在中國內地,唸完學士,幾乎都爭取唸碩士,最好是再唸博士。連僱主都會覺得,學歷愈「高」,本事愈大,把學歷等同於能力。在外面,碩士、博士,是按照專業或者學術要求才唸的。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