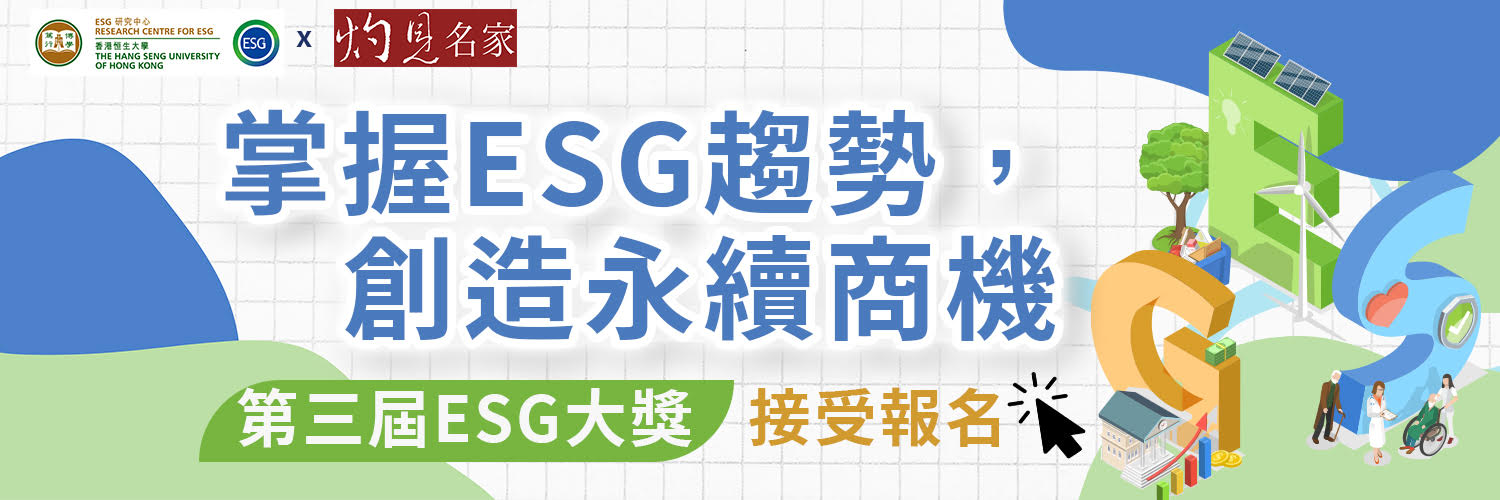編按:香港中央圖書館2015年11月邀得鍾景輝先生為嘉賓,出席題為〈戲劇大師的道路——King Sir 精選劇本圍讀〉的文學月會,與他的學生、觀塘劇團總監呂志剛先生對談。本文為對談內容整理。
求學時期:為戲劇什麼都無所謂
我1947年由上海來香港,入讀培正小學五年級。讀培正時有四位老師專門搞戲劇。後來培正參加教育司署舉辦的全港中學戲劇比賽,翻譯劇《丟落的禮帽》,當年我得到最佳男演員獎。高中畢業後:我第一打算讀戲劇,第二讀體育。在香港不能讀戲劇,只能等機會去外國學習。那時也曾打算去日本讀體育,早稻田大學體育很有名。如果沒有機會讀戲劇,便會留學日本。後來我終於進入崇基書院念英文系。
選讀英文系,因為自己中文中學畢業,所以英文底子比人差,希望多讀英文,以備將來的機會。那時接觸文學的機會多,多讀英文的小說戲劇、各種書籍。別人外出遊玩時,我就躲起來譯劇本、查字典。其實我高中畢業後就開始翻譯,譯過劇本《危險的角落》(Dangerous Corner),劇本後來在崇基書院劇社上演。翻譯劇本有助我學習英語。
我在崇基待了兩年,便到美國奧克拉荷瑪浸會大學(Oklahoma Baptist University)主修演講與戲劇。不過我仍然很熱衷戲劇知識的學習,完成學士學位前一年,就報讀碩士了。當時耶魯大學戲劇學院(Yale Drama School)是美國北部最有名的戲劇學院,另一間是 Baylor University。寄信之後,我收到 Baylor 的回覆,要等他第四年學分的結果才決定。隔兩星期,我卻收到耶魯表演系的取錄通知,連面試也不必。後來探尋原委,原來推薦信幫助很大。我邀得培正中學的關存英老師為他寫信之餘,本來不敢勞動林子豐校長,校長卻主動親筆去信耶魯大學。連沒有教過我的崇基書院老師,聽聞我報考耶魯,同樣主動寫信推薦。
我1958年去耶魯讀書。那個年代讀戲劇,回來都不曉得可以做什麼,可能乞食都未輪到我。不過,無所謂,戲劇是我最喜歡的學科。就算回來無得發展、什麼都無,我只能憑外國讀書的經驗在學校教書,教 ABC 都可以吧?(眾笑)如果能和學生辦劇社,就算豉油撈飯,我都會好開心。
我只有這個想法:如果我下半世回來不是做戲劇,做其他不太喜歡的事,我會很不開心。這就是我的底線。因為有底線,我不怕吃虧,去追求我喜歡的、我想知道的,來補充我的不足。我也很感激爸爸,他覺得我喜歡就可以,並沒有阻止我。
另一個問題,是香港的戲劇發展很慢,但愈是慢,發展的機會愈大,空間愈闊——說我阿Q也好,我是掉轉頭來想。
我在美國那麼久,學到了一個工作重點,就是:一個人愈是發展得慢,他的工作範圍就會愈大,愈是可以在社會貢獻自己學到的東西。我也學懂「在有限的條件之下做到最好」。在香港的有限條件,就是什麼都沒有,連劇場也沒有(50年代時),當時只能在有限的條件之下做到最好。我在美國留學時除了學識、技術、工作態度外,就是學懂這個,不會埋怨什麼也沒有。我就算只得一張椅子也能做戲。
觀塘劇團總監呂志剛:浸會首先邀請你去教英文,之後電視台興起,你便報讀電視廣播,如此把握機會亦是我們很佩服的。
浸會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在耶魯大學的碩士課程要讀三年,第二年學期末,浸會大學副校長 Dr Anderson 寫信到耶魯大學,問我有沒有興趣回港任教浸大。當時收到這個消息很開心,當然答應,之後便在浸大任教英文課程和一些英文系戲劇課程。之後更在浸大開辦表演課程、導演初級和中級課程,亦開辦了演講課程。當時我是業餘話劇社的成員,亦會參加電視劇、戲劇的演出。在浸大任教幾年後,1964、65年,當時還只得麗的電視一個有綫電視台,未有無綫電視。我認為無綫電視在香港是有發展空間的。我對電視很有興趣,於是1965年就申請了獎學金,去紐約大學研究院。
無綫時期:年輕人要「抵得諗」 不要怕吃虧
這也是機緣,一個人有時運氣也很重要,我1965年過去,準備讀一年就回來,但當時麗的電視高層黃錫照先生來信,問我可否再多讀一年,1967年才回港,因為1967年無綫電視將會開台。但當時不可以,因為我答應了浸大,在紐約大學讀一年,再回港教授一年,才算完成合約。黃先生便說回來再談。之後我1966年暑假回來,黃錫照先生再找我,1967年我便加入了無綫電視。就憑著我在紐約大學一年內所選修的兩科電視課程的基本常識,我就加入了無綫。第一年我是高級編導,剛加入兩個星期,公司便派我到日本六個星期,到日本 TBS 電視台去看他們的製作:在戲劇方面的製作、廣告的製作。同年10月升任節目部經理,沒有加薪,兩年後才加薪。我從來都不提薪金,由我第一份工作到現在,任何一個職位,我都不曾要求別人加我薪金。我記得一句說話:年輕人要「抵得諗」,不要怕吃虧。如果你表現好,總會有機會。當年做了節目部經理,無綫電視在海運大廈開始試播,之後於11月19日開幕,這便是我加入無綫電視的經歷。
呂志剛:很多人都想聽聽歡樂今宵是如何製作、如何找演員的。
《歡樂今宵》開始時,是蔡和平和我一起做。他負責一、三、五,我負責二、四。《歡樂今宵》是無綫電視第一個最多觀眾的節目,因為既是新的又是直播,觀眾覺得很新奇,雖然當時還是黑白電視。我本身不太享受做綜藝節目,尤其是做趣劇,有時真的很無聊(眾笑)。不習慣又難處理,加上做完之後已是晚上10時多,還要去夜總會討論用哪個歌星。當時選擇不多,因此要出去找。雖然不適應,但被指派還是要做。
之後無綫開始增加戲劇的節目,由第一套《太平山下》半小時的電視劇到《夢斷情天》長篇劇。我覺得長篇劇是可行的,但當初不敢試連播五日、只試播兩日半小時再加一日三小時。之後因為多人追看,結果將晚上的半小時節目變成15分鐘,調到下午四時,播五日給主婦們看,之後再合成一小時放到星期日上午重播,而當時由馮淬帆和黃淑儀主演的《夢斷情天》便成了無綫第一套長篇劇。
呂志剛:之後你開始「作反」,將自己喜歡的戲劇節目放進電視劇中,例如《清宮怨》、《玻璃動物園》。
當時我另外起了一個節目叫《電視劇場》,學美國的第13台,專播一些水準較高但不一定會吸引大部分觀眾的戲,希望能介紹一些好的劇本給觀眾。我心想,一星期抽1小時播放應該可以吧!反正當時我是節目部經理可以做決定。(眾笑)
呂志剛:《清宮怨》呢?當時很流行的。
《清宮怨》是1971年無綫成立訓練班之後的。當年是我提議無綫舉辦訓練班,因為不夠演員。電視劇和戲劇不斷發展,但不夠年輕演員,所以便提出開辦訓練班。初期的訓練班是一年制,在星期一至五的晚上和星期六下午。當時有很多演員出現。我揀選演員的標準跟現在不同,不論高矮肥瘦、美或醜、身材好與否,最重要有演戲潛質。我只著重潛質,覺得他們可發展便給他們機會,將來命運便靠他們自己了。所以一班年輕人都很爭氣,到他們畢業後第二年,有一套劇叫《朱門怨》非常紅,劇中絕大部分是年輕人。電視劇收視率比《歡樂今宵》還高,這是第一套,當時超過100萬人收看。《清宮怨》亦有很多年輕人,我便想開辦一個劇團,在他們未有劇要拍時鍛練他們的舞台功夫。於是辦了一個舞台劇,組織了「翡翠劇團」,絕大部分都是訓練班的年輕人,例如杜琪峯、周潤發,亦是團員。《清宮怨》是第一套在舞台上做的劇,做了23場,當時於70年代已算是成功了。
呂志剛: 麗的電視開台時請你過去。你當時很厲害,算是扭轉了它的發展,請談談你在麗的電視時期的事跡。
電視台的工作並不是做一個節目成功就可以。第一,一定要把新聞做到最好,新聞節目很重要。另外,不像外國電視般用長篇劇鎖住觀眾。香港不同,你想觀眾不轉台,是需要每個時段都做得好,否則只會令觀眾看完某個節目便轉台。
呂志剛:King Sir 1978年去了香港話劇團,除了做顧問,也幫他做第一套戲《馬》。當時題材很大膽,很多心理辯論、哲學認證,對香港的觀眾來說題材都有些深奧。
當年這套戲有些深度,是講述一位年輕人有些精神問題,或是思想上有些問題,而醫生用了很多時間去醫治這位年輕人。但治好後,醫生反而覺得治癒後的他缺乏了自己的特性和思考能力,令他想到一個問題:到底醫好他是好是壞?這個便是劇中的重點。
呂志剛:1980年,你將百老匯音樂劇原汁原味、亦帶有一些香港風格地,搬上香港的舞台。
當時是我的第一次,亦是香港第一次將百老匯音樂劇搬上舞台。我和香港話劇團合辦《夢斷城西》,萬梓良、伍衛國等都有份參與,黃霑和我一起改劇本和歌詞。當年有很多人都有另一種看法,覺得把外國音樂劇改成中文不行,不會好聽,但黃霑把歌詞改得很好,很有詩意,就算是粗俗對話都能改到令觀眾接受。
呂志剛:猶記《夢斷城西》當年盛況。你隔了兩年便做《莫扎特之死》。你說自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只是不斷努力。你認為天賦是公平還是不公平?你對《莫扎特之死》的題材有何看法?
《莫扎特之死》寫人的妒忌心,寫得很精彩。講述莫扎特在世上時,在宮廷內有個樂師,原本作品很受歡迎,但莫扎特出現後,他的作品便顯得很平凡,人們愈來愈不喜歡他的作品,最後樂師更銷聲匿跡。他整天覺得為什麼上帝要眷顧這位不認真的年輕人而漠視自己的努力,因此便計劃去害死莫扎特,令莫扎特之後的生活過得很悲慘。
呂志剛:1984至1986年,你開了一家製作公司,創立用明星做戲的先河,製作了幾套輕鬆小品,可以分享一下嗎?
我1983年離開亞視,並未有什麼計劃,便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我跟有共同興趣的朋友成立了一家公司,做了幾個舞台劇,其中一個有馮寶寶和梁家輝,另外有一組還去了紐約演出。

評價演藝學院:遲到好過無到
呂志剛:那兩年離開了亞視,演藝學院也是籌備中?
我1983年1月離開亞視,演藝學院的人3、4月找我,問我有沒有興趣當演藝學院的戲劇學院院長。我當然有興趣!我讀書和工作都是這個範疇,當然希望香港有演藝學院。於是我在6月便加入了演藝學院,開始籌備工作。
呂志剛:你1962年回港,心願是要等一個真正戲劇平台,你算是等了很多年。
對的,等了很久。1983年開始籌備,1985年戲劇學院才開。
呂志剛:King Sir很多地方都很順利,因為他有實力,也會抓住任何機會。
我在兩家電視台共做了16年,16年都在浸大兼職教書,一腳踏兩船。(眾笑)幸好我一腳踏兩船,因為如果我沒有教過書,離開亞視後很難做戲劇學院院長。我總共兼職教了23年,直至離開亞視為止。就因為有23年教學經驗,增加了他們對我教戲劇學院的信心,所以有時真的要一腳踏兩船才有用。(眾笑)
呂志剛:你在演藝學院做了18年才退休,當年你有否感概演藝學院姍姍來遲?感覺如何?
我當然很高興,雖然是很遲,1985年才開學,但遲到好過無到,這所學校對香港的演藝藝術貢獻是肯定的。
呂志剛:演藝學院有一個使命,發展和培養創意一流的藝術家,為香港、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文化環境帶來新氣象,似乎這些已做到了。演藝學院的成立對香港的藝術生態帶來什麼改變呢?
最明顯的就是,以現在來說,在香港的任何一個演出,你打開場刊,必會有演藝學院前後台的工作人員名單,這已是一個很明顯的貢獻了。而且我們看到,有了演藝學院之後,一批畢業生出來社會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好的貢獻——他們還在不斷努力——這個貢獻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作品,無論是舞蹈、音樂、戲劇演出,前台後台水準的提高,都比以前明顯很多。這些是對演藝學院的一個肯定。
答嘉賓問
張達明:King Sir 讀書時還未有演藝學院,到底你是在哪裡培養或訓練你的優秀演技呢?
答:當時什麼都不懂,做什麼都是亂來的,夠膽去做,做了出來再慢慢去改。
張達明:當時你帶荒誕劇來香港時是什麼年代?香港的觀眾難不難明白?可以講講當時的狀況嗎?
答:當時我第一個介紹的是《動物園的故事》,這個是我在60年代時在浸會做的,就是馮淬帆、袁報華兩個做,因為荒誕劇的確是難的,當時的禮堂只能坐百多人,三面觀眾,同一晚做兩個劇,一個是《動物園的故事》,另一個是《快樂旅程》,就是介紹這兩套給觀眾,當時我的對象是大學生和大專生,所以不志在賣座,是給他們解釋一下什麼是荒誕劇,應該要留意什麼、內容是什麼等,他們去看的時候會比較容易理解。
張達明:最近有些人認為無綫的訓練班不滯,演員演技和態度都不好,但40多年來,很多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影帝,大部分都是無綫訓練出來的演員,例如梁朝偉、劉嘉玲、梁家輝等。是否現在無綫的訓練是有問題呢?還有他們應該如何處理才好呢?抑或是現在無綫的訓練班不行了呢?
答:跟以前比較,訓練的時間短了。他們現在是三個月的訓練。以前的是經過很多工作上的訓練,令他們鍛鍊了成熟的手法,到現在就可以拿獎了。
張達明:那麼現在算是拔苗助長?
答:現在是無綫給你錢去上課,但當年是你交學費去訓練班上課,所以是不同的。幾個月之後就讓你去節目裡「自訓」。(眾笑)
呂志剛:有些戲令我們反省人生。一套不得不提的戲,就是《相約星期二》,它2007年開始公演,King Sir演出了124場,上個月第19度公演,依然座無虛席,也有很多人看了幾次,我自己都看了4次,每次看都會有新的發現和感覺,對人生的覺悟是很好的。因為King Sir會告訴你,認識死亡等於認識生活。這部戲已到過很多地方,例如溫哥華和多倫多,相信會繼續演下去。有沒有關於《相約星期二》的一些重點想要提醒觀眾呢?
答:這套戲是兩個人在討論人生的問題、生老病死、生兒育女、婚姻的問題,都是老生常談,但為什麼會吸引你?用什麼方法去留住觀眾?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角色所提到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我們一生必經的過程,都會遇到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應付。所以觀眾都會一邊看,一邊和角色一起思考,到底自己做多或做少了?

答觀眾問
問:一個演員要具備什麼條件呢?挑選演員是從哪些方面著手呢?身為戲劇大師,在掌聲的背後你有什麼得著和感概呢?
答:關於演員的條件,我主要是看他們的潛質,看他們有沒有可能在這方面發展,如果有便盡力幫他們完成夢想。有時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潛質,我們便幫他們發掘和培養。演員有幾方面一定要有,第一,幻想力,特別是在舞台,因為舞台上每樣東西都是假的,你要想像你是那個角色,在那個環境裏。而且在舞台上,氣候也是假的,你要如何用身體和語言去表達氣候,全部都是靠演員的想像力,所以這是演員必備的條件。第二,就是節奏感,節奏感跟你說話的快慢和停頓是有很大的關係,一部戲的演出就是等於一首音樂的演出,演員就是用聲線、用動作的節奏來去演繹角色。而導演就像指揮,指揮演員的動作。第三,就是一定要有相當程度的聰明和智慧。因為要應付很多東西,要應付不同編寫家的作品,全部有不同的風格、不同的信息。你要懂得如何演繹,怎樣去研究角色和主題。最後,就是要懂得如何跟別人合作和交流。我們去上演藝課時,很多時候都會被派去服裝組、音響組、燈光組各做幾星期,讓我們知道別人的辛苦。當你站在舞台上,你要知道有多少人在幫你,完成你的演出,你就會懂得尊重別人的崗位,懂得與人交流和合作。無論做導演或演員,你主要想得到的回報不是掌聲,千萬不要向那方向做,否則你就會不斷做一些行為去令觀眾鼓掌,就會過火。
問:記台詞,你有沒有一些秘訣可以教給我們?
答:第一,最重要是聽對方的對白,因為他會從中提醒你下一句對白和應對。和對方交流是很重要的。我亦會將對白畫成一幅畫,以畫來提醒自己應該說什麼和想什麼。第二,舞台上的位置都能提醒你,一到某位置就會說某句對白,或用動作來提醒自己要說什麼,亦可以在舞台上某些位置上望著某種物件,每次看到都能提醒自己要說什麼。
問:你有那麼多學生,有很多個都成名了,會否覺得自己眼光很準?
答:有準有不準。例如周潤發考訓練班時其實已被淘汰了,因為他沒有演戲經驗,讀台詞亦不是很純熟,評分很低,但我覺得他有潛質,只是不懂運用。他夠高大,我覺得可給他一個機會,之後便看他自身的努力。
問:請你分享一下對劇壇將來的展望。
答:香港的劇壇在香港演藝學院成立之後提升了很多,畢業同學的努力是看到的,但速度仍然是慢,在700幾萬人口中,只有2、3萬的看戲數字。香港的劇壇未夠觀眾去支持演員和後台工作人員的生活。因為現時沒有一間中學或大學有戲劇課程。美國認為戲劇、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是人生中必然的重要因素,若沒有受過這些教育便不算是一個好的美國公民,於是1994年宣布於2000年開始,小學、中學和大學都要有演藝課程,這就是香港所缺乏的。香港的學生到畢業還沒有看過舞台劇的大有人在,這証明了戲劇教育緩慢和失敗的地方。如能從小培養對戲劇的興趣,長大後都會有興趣去看戲,支持劇場。
問:一個演員如何於演出後抽離角色,再投入於另一套戲?
答:對我自己來說,我可以很投入一個角色,當完成後亦懂得讓自己抽離,但我都試過有個學生做話劇抽離不了,之後離開了這個圈子。所以要學懂如何走出來,做回自己。
問:導演面對沒經驗的演員,可以怎樣帶領他們進入角色,令他們做得好一些?
答:盡量解釋,讓他們知道他們在該場戲要做什麼,和對手的關係是什麼,令他明白如何投入,為什麼要出現在這場戲內,這樣他們便會更易入戲,所以要由大綱開始再慢慢深入去解釋。
(圖片:灼見名家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