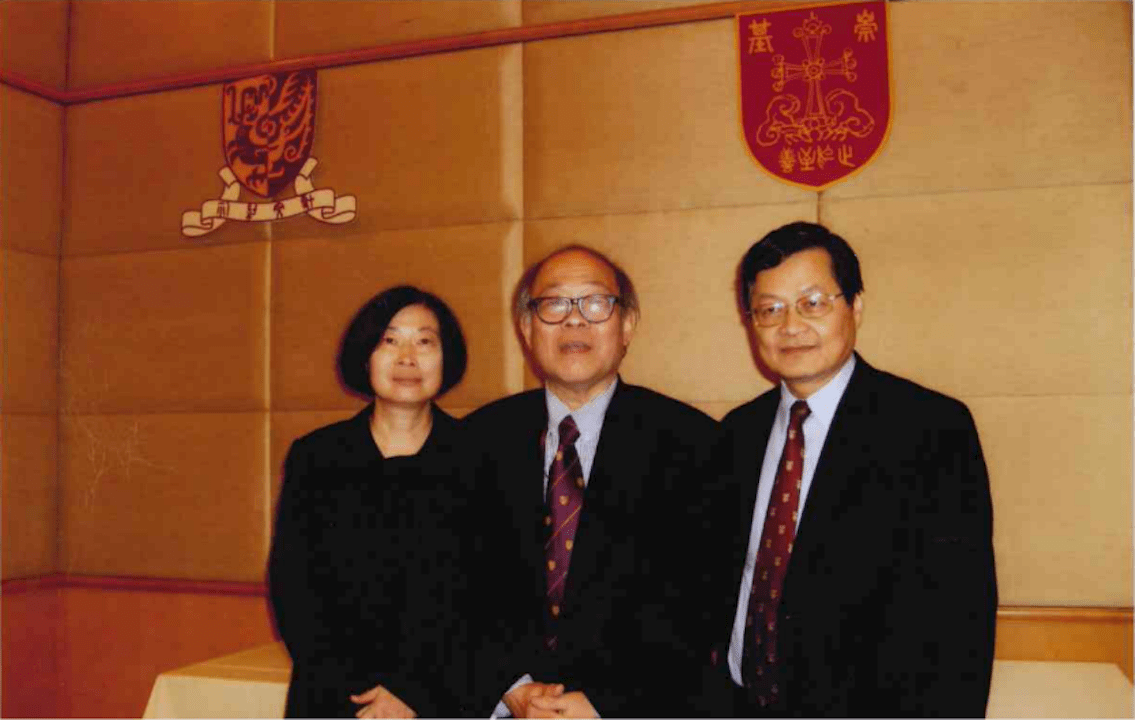香港史如何寫?此問題殊不簡單,所涉範疇也委實很大,甚至可以跨越生死。不過,對明銶教授而言,死生的課題似是一大禁忌,相信只有我偶敢犯禁,而被他追打。
初識陳教授時,我還是研究生。自那時開始,便一直叫他「陳師傅」。他卻給我起了一大堆花名,當中當然包括「蔣夫人」。和他較熟稔後,這位「花名大師」驚悉我的喜好之一,竟是逛墳場,便被嚇傻了,於是給我多加了一個「奇女子」的花名。我近年的研究課題之一是死亡史(與香港史和華僑、華人史有關),更直把他嚇到跑得遠遠的。有幾年我在研究經費的資助下,與一位同行常到美、加跑華人舊墳場。陳師傅一見我們便很惱,竟直喚我倆為「壞女孩」!
香港「邊緣」地位的重要性
我的香港研究「犯了禁」,然我也察覺到,男女對生死的觀念可能有別,而男與女、生與死,以至其他界別的微妙性,實耐人深探,當中不少與認同課題有關。就以香港的「邊緣」地位,以及港人的「邊緣」身份為例,不知已成為多少學者討論的熱點?近年我在尋繹有關問題時愈來愈肯定香港「邊緣」地位的重要性。這塊土地所曾提供的批判空間,及其逐漸塑成的特殊文化生態所發揮的影響力,實不容忽視,有待詳審。歷史上許多問題的答案,也許都可在邊緣領域尋得。可我們都崇拜主流,或要將邊緣主流化,卻不知變化之源常在邊緣和界際之處。
陳師傅近年在港、澳歷史的研究上,開展了身份認同的領域,這位向來重視史學的實證性的學者(不是說他只重理性,其實他屬感性型人格。就曾見他為擔心學生而暴瘦),似有一種向思辨論的轉向。這種變化其實不足為奇,因認同問題是我們當下共同面對的非常切身的挑戰。陳師傅在香港教學多年,卻一直強調自己的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的身分,遷回Palo Alto後又常自稱為「加州的中國人」。他退休後即離港返美,卻仍長年穿梭二地,與香港的關係顯得難分難解。在香港的追思會上派發的《陳明銶教授追思錄》中的文章有稱他為「香港之子」、「香港魂」、「堅定的民主派」、「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學者」、或「深明大義,愛國愛港,擁戴一國兩制事業」者等等,何嘗不是在在關乎無論是撰文者或其撰述對象的身份認同問題。當然我們無法,也不必要求陳師傅作出澄清。在這方面,容我引錄科大衛教授文章的末句作結:
Hong Kong people of the future who will read him without having seen him will accept his life and work as a reflection of the ambiguities of our 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