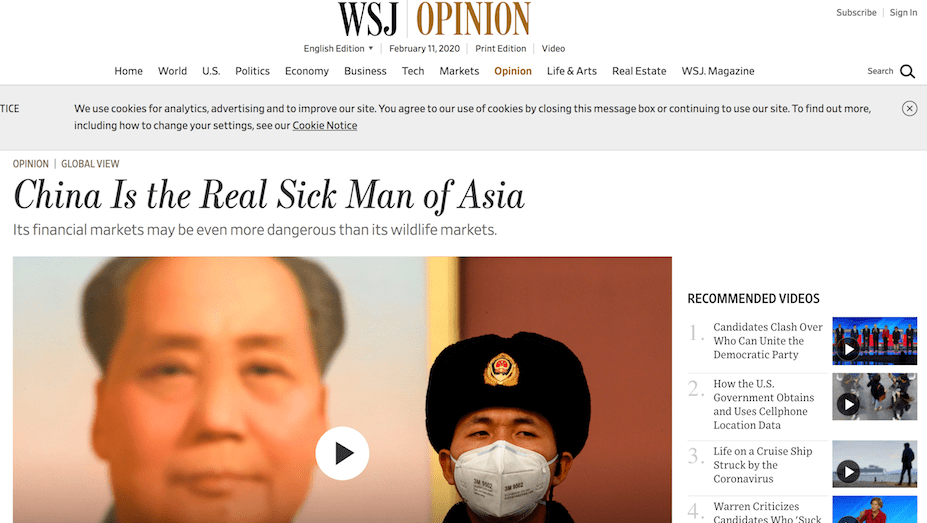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與病毒作鬥爭的歷史。每當一種新病毒出現,它不僅僅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敵人,而是所有社會、所有國家的敵人,需要國際社會的合作來共同應付。但是,正需要國際合作的時候,在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針對中國或華人的種族話語和行為也在快速死灰復燃。
《華爾街日報》2月3日公然以「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為題發表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撰文章。不管作者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如何,一份西方主流媒體竟然使用如此赤裸裸的種族主義的標題,意涵深刻。《華盛頓郵報》2月5日發表潘文(John Pomfret)的文章〈新型冠狀病毒重新喚醒針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老旋律〉(The coronavirus reawakens old racist tropes against Chinese people),討論美國再次日漸成長的反華人社會情緒。其他一些主流媒體也注意到這種新趨勢。實際上,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對華「隔離」政策和過度反應,也不言自明地隱含着濃厚的種族主義因素。
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種族主義行為根深柢固。前不久,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在論及中美關係時強調,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是與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並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這番言論再次把美國學者亨廷頓在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衝突理論,拉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沿。儘管在盛行「政治上正確」多年的美國,基於種族的外交理論已經不為大多數人所認可和接受,但這種在歷史上曾經產生巨大作用的理論,已經在潛意識層面成為一些人的種族情結,一旦有機會,就會重返美國的外交話語。
不能忽視種族主義理論加快抬頭
隨着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人們沒有任何理由輕視或忽視這種種族主義理論的加快抬頭。就國際關係而言,今天美國和西方世界最擔憂的,就是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所面臨的嚴峻挑戰。西方「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在於其內政,或者說,外部「自由國際秩序」是其內部「自由民主秩序」的延伸。今天西方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是內部秩序出現了問題,影響到其外部秩序。不過,西方並不這樣看;相反,西方普遍認為,對西方「自由國際秩序」的最大挑戰來自外部,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美國也已經把中國和俄羅斯正式視為是美國最大的對手。對美國來說,如何應付中國自然變成美國外交的最高議程。要有效應付中國,就要有一種理論指導,就如二戰之後凱南(George Kennan)的〈X文章〉(X Article)成為美國遏制蘇聯的冷戰理論一樣。
自由主義起源於西方,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是由西方所確立,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地使得這個秩序具有種族性質,不管人們承認與否。在西方內部,因為各國內部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的不同,從來不存在一種統一的西方自由主義;或者說,自由主義在西方各國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在國際層面,因為西方各國國家利益不同,他們所理解的自由主義也不同,企圖用自由主義來構建世界秩序的方法也不同。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從來就具有多元性,從來不存在一個「一元化」的自由主義或「自由國際秩序」。
但是,就種族而言,西方自由主義又存在一個高度統一的認同,即世界被簡單地分成「白人與非白人」或「西方與非西方」,而「白人」和「西方」的目的就是整個國際秩序「自由主義化」。更重要的是,因為內政是外交的基礎,「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是內政,所以西方在確立「自由國際秩序」的同時,必須把這個體系的成員國的內政「自由化」。
在這個理論認知下,干預他國內政或當代所說的「政權變更」,也成了西方外交(尤其是英美國家)的一個主體。英國劍橋大學政治理論家鄧恩(John Dunn)認為,英美政治理論是基於「價值」的理論。人們也可以將此延伸到外交,即英美外交是基於「價值」的外交。「價值」又意味着什麼?英國學者任格(N. J. Rengger)對此解釋得很好,那就是要回答兩個相關的問題,即「我是誰」和「我要做什麼」。對這兩個問題的終結回答又可回到宗教,答案即「我是上帝的子民,要執行上帝的意志」。從這個角度來說,無論是過去西方和非西方的宗教衝突(例如十字軍東征),還是今天所說的「文明衝突」,背後的價值邏輯都是一樣的。
歷史地看,自由主義的發展和擴散有一個過程,即從西方到非西方。從發展次序來看,自由主義要先解決西方內部的問題,然後才解決西方和非西方的問題。
法國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所確立的「自由、平等和博愛」,可說是自由主義的核心,被視為具有普世性。啟蒙運動思想家不僅要在法國實現這些價值,還要把這些價值推廣到全世界。啟蒙思想家孔多塞(de Condorcet)就認為,西方要扮演「慷慨的解放者」角色,把那些受「神聖」但專制和愚昧的征服者統治的人解放出來。另一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更為激進,他甚至提出了「強逼自由」的理論,認為如果人們不要自由,就要「強逼他們獲取自由」。
這些理論不僅對西方的內部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更成為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例如,法國努力通過殖民地政策,把這些價值銷往被其統治的殖民地,尤其在非洲,並且把這些國家視為勢力範圍。在很多年裏,法國在非洲對美國的防備,甚於對蘇聯的防備,因為法國很擔心法國的「自由價值」會被美國所代表的「自由價值」所取代(法國並不認為蘇聯代表一套可以讓人們接受的價值)。
白人優越論成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
這裏指向了西方不同國家所持的不同自由價值觀。的確,在美國走向整個世界舞台之前,為了和歐洲國家爭奪勢力範圍,美國針對周邊國家提出了「自由主義價值觀」,和美洲國家一起提出和確立了「睦鄰友好」、「不干預」、民主、和平和正義等原則。
儘管在向非西方擴張的過程中,西方國家之間存在競爭,甚至導致了它們之間的戰爭,但西方的所有擴張都有一個統一的理論認知,即「白人優越論」。這一理論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達到了頂峰,成為國際秩序廣泛使用的理論。當時,西方認為世界上只存在一個文明標準,即西方文明,說西方即說文明,說文明即說西方。「白人優越論」成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背後既有西方的硬力量,也有西方的軟力量,硬力量以經濟軍事力量為代表。經過近代以來的工業化,西方在經濟、軍事和社會等各方面成為全方位的強權,沒有任何非西方國家能夠和西方國家相比。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打敗俄國,這是唯一的例外;但日本的成功恰恰被視為「西方化」的結果。
軟力量方面,19世紀出現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且很快在西方流行,為西方所接受,成為主體意識形態,為西方「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提供了理論基礎。達爾文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他並沒有明確把「進化」理解成「進步」,儘管他似乎默許這種理解。社會達爾文主義則把達爾文的物種進化理論應用于解釋社會發展。因為西方「物種」強大(打敗了其他國家),所以西方是先進的、進步的、文明的、道德的。在殖民地和帝國主義那裏,「白人」與「非白人」的區別完全取代了其他所有類型的區別,包括民族、宗教和國家的多樣性。
在歐洲發明和發展起來的「白人優越論」也很快傳到美國。19世紀,美國盛行「白人至上」(White Only)理論,借此應對數千萬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新移民。美國同樣將此應用到國際事務。人們不應當忘記,今天美國在國際關係和外交領域最重要的政策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前身就是《種族發展雜誌》(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種族發展雜誌》于1910年創刊,關注美國的外交事務,後改稱《國際關係雜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22年再改名成為今天的《外交事務》。
19世紀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主義,到了20世紀的二戰之後就被文化多元主義所取代。這種轉型主要不是因為西方改變了對非西方的看法,而是因為西方內部的血腥種族屠殺。二戰期間,德國希特勒對猶太民族進行大屠殺,導致近600萬歐洲猶太人死亡。
197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內部少數民族的民權運動崛起,尤其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西方國家對種族問題的看法有所改變,至少有所收斂。「文化多元主義」因此崛起,在美國表現為「大熔爐理論」,相信西方文明能夠包容甚至消化來自不同種族的社會群體。在學術和政策界,人們自覺地不去談論一些敏感問題(種族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形成為「政治上的正確」原則。
但是,在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情況有了急劇變化。在世界範圍內,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被視為得到證實。之後,亨廷頓更是專門出版著作《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對美國白人數量的減少和其他民族人口的增加表示了極大的擔憂,並且把此現象稱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之後,不同形式的恐怖主義發生在歐洲諸國。西方開始對西方文明的包容能力發生懷疑,知識界和政治人物開始公開承認文化多元主義的失敗。這也構成了這些年來整個西方圍繞着移民和恐怖主義的政策爭論的背景。
非西方的種族主義思維
經驗地看,在西方的外交政策中,種族因素從來就沒有消失過,也不會消失。在不同背景下,人們可以收斂一些,或者虛偽一些,但種族主義還是會不時以不同的方式浮上台面,並發揮政策作用。從中世紀的「宗教」(上帝),到近代的「種族」(白人優越論),再到當代的「民主自由價值」(價值同盟),其理論和行為邏輯都是高度一致的。
更糟糕的是,很多非西方國家因為長期受西方統治,人們已經在潛意識層面接受了這一認知。日本學習西方而崛起,很快成為軍國主義者,試圖以此來證明「大和」民族較之亞洲其他民族的優越性,至少可以實現和西方平起平坐的目標。直到今天,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群體仍然處於「思想殖民」狀態,對西方抱有毫不實際的幻想。
在一些地方,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與西方比較有過之無不及,一些人為了一些具體的利益,通過各種工具和手段,人為地創造變相的「民族」或「種族」,例如強化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同「認同」和製造他們之間的衝突,例如「先來者」對「後來者」、「本地人」對「外來人」、「民主」對「專制」等等。這些所謂的「准民族」已經導致政治糾紛和衝突,未來也必將造成更大、更為強烈的衝突。
不過,更為宏觀地看,隨着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文明國家的崛起,西方的種族主義有可能得到制衡和遏制。以現實主義來說,國際關係上各方面的平等(包括種族),與國家間的權力制衡有關。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都是基於文明的國家,擁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這意味着一個多元國際秩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多元國際秩序的基礎不僅僅是硬力量,更包含以價值為核心的軟力量。也就是說,未來的世界是一個諸「神」共存的世界。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