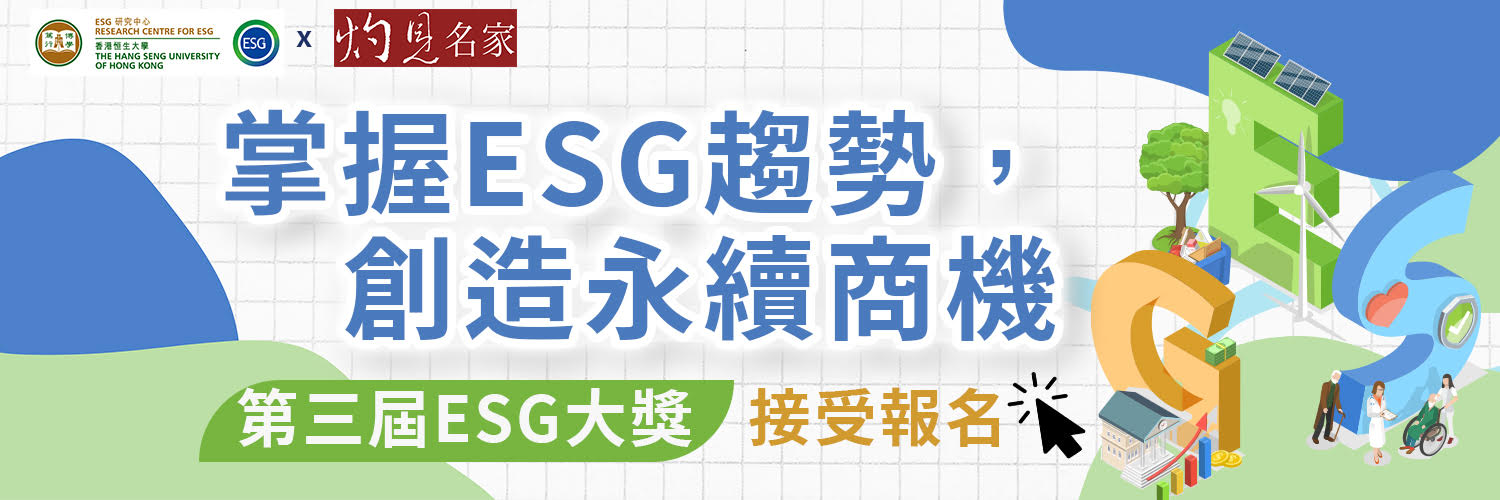1997至1998年間,我雖身在澳洲悉尼,卻在一本香港雜誌每星期發表一篇「科幻小小說」。1999年,這些故事得以結集出版,書名是《無限春光在太空》。不用說,故事的背景不少都跟太空有關。(這書的新版是《泰拉文明消失之謎》。)
我為什麼要如此詳盡地交待這些個人的歷史呢?我的目的,是說明我是一個如何熱衷於太空探險的人。1980年「星空奇遇」的大電影(Star Trek──The Motion Picture)上映,我在影院裏目睹闊別多年的「冒險號」(Enterprise,這是當年麗的電視的譯名;今天的人大多稱為「企業號」)在「太空船塢」的雄姿時,禁不着熱淚盈眶……。
我之所要作出這樣的說明,是因為我認為劉慈欣的慨歎包含着十分誤導的成分,而在面對極其嚴峻的環境災劫當前,這有可能令到年輕一輩對形勢作出完全錯誤的判斷,從而令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地球危機正逐步逼近
20多年前,筆者其實也經歷了「大劉」這個階段。我於1991年動筆而於1992年完成的英文短篇科幻小說Prometheus Unbound之中,便已假設在一場全球性的環境浩劫之後,世界轉由一個名叫「蓋亞議會」(Gaia Council)的最高權力組織所統治。這個組織禁止一切科學的研究,亦禁止人類對太空的探索,情景與「大劉」所說的「放棄了太空而把未來寄托於環保」有九成相似。這個故事後來被譯成中文(就叫《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並於1992年在台灣的《幻象》雜誌發表。及後則先後收錄於我的《挑戰時空》和《泰拉文明消失之謎》這兩本著作之內。
且看我當年(透過了故事中的主人翁)是怎麼說的:「人類當前最缺乏的,正是你方才所說的那種進取精神。我們如今的這種極端內向的心態,完全是現政權所鼓吹,甚至強逼人們去接受的。正當人類開始掌握了馳騁於星際空間的能力之時,我們卻放棄了整個宇宙!」
但20年來,我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為什麼?正如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被問到他為何改變了初衷時所說:「當事實改變了,我自然就改變我的看法。哪麼你呢?」
在一方面,就科幻創作的層面來說,我認為《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裏的假設仍是一個很不錯的科幻設定,而且長遠來說仍然可能出現。但另一方面,現實中的事態發展──特別是全球暖化的衝擊──已經遠遠超乎我們(包括全世界的科學家和環保分子)的想象。可以這麼說,即使全人類今天即能排除萬難、同心戳力地去對抗這個問題,我們也無法完全防止災難的陸續發生(因為自然界存在著巨大的「時滯」效應),而只是能夠阻止最嚴重的災難出現。當然,如果我們什麼也不做,這些毀滅性的災難將會接踵而來,至令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成為「小巫見大巫」。
作為一個族類,人類滅亡的可能性我認為十分之低。但巨大的人道災難(包括戰爭)將會奪去無數人的寶貴生命,而劫後餘生的人,將會生活在一個文明大幅倒退甚至社會秩序崩潰的、弱肉強食的野蠻世界。荷里活於70年代末推出的電影 Mad Max(在港上映時稱《公路戰士》)及其續集,在不少人眼中可能只是一些俗文化的娛樂產品,但我們若認真地考察一下現今世界的發展趨勢,當會看出30多年前的預言在今天是如何的更富警世意義:我們真的敢說電影中的情節不會出現嗎?
當然,比電影更早的預言是John Brunner於1968年所發表的巨部頭環境災難小說 Stand On Zanzibar 。它比「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於1972年發表的經典論著《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還要早四年。而在整整40年後的今天,無論是小說家的前瞻性臆測還是學術理論模型的電腦演算,都正在一步一步的應驗。
危言聳聽嗎?要知人類是否真的大難臨頭,各位可以閱讀我最新的著作《喚醒69億隻青蛙──全球暖化內幕披露》。然而,由於這是一本寫給年輕人看的書籍,我在書中已盡量把我的悲觀結論淡化,以免年輕人掉進消極的泥坑裏。(這本書雖然也有觸及其他環境問題,但主要還是集中於全球暖化威脅,要更全面地了解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筆者極力推薦大家閱讀James Gustave Speth所寫的 The Bridge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2008),以及由Lester R. Brown 所寫的World On the Edge(2011)。)
哪麼這是否表示我不再支持太空探險呢?當然不是!相反,在上述這種情況底下,太空探險更有其逼切性。
但請不要誤會,這種逼切性絕非「開發太陽系以解決當前的問題」,而是當最差的情況出現而文明全面崩潰時,我們若是經已建成了可以自給自足的太空城市、月球基地或是火星基地等,那至少可以為人類保存一點現代文明的「血脈」……。
大劉在講座裏提到:太陽系內擁有10萬個地球的資源(這應當來自某些科學家的推算),我絕不懷疑這個說法。問題是「遠水救不得近火」這個簡單的道理。試想想,在美國太空穿梭機計劃剛剛劃上句號的今天,「開發太陽系」這個充滿雄心壯志的號召如何能夠幫助我們解決當前的問題呢?只要我們再想想:要把一公噸的負載送上太空會製造多少公噸二氧化碳,我們便會更明白這個號召是如何的脫離現實。
事實上,我於八十年代開始關注環境生態的破壞時,造夢也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得這麼快:比起二十世紀初,全球高山冰雪至今已經消失了一半,而北極海冰的面積更是縮減了接近三分之二!海洋的升溫和酸化已令全球三分之一的珊瑚區死亡、西伯利亞的廣闊凍土區域已開始出現融化並釋出較二氧化碳還危險百倍的甲烷氣體……。此外,愈來愈反常的澇、旱和暴烈的天氣已經成為了日常新聞報道的一部分,駭人的持續高溫天氣一浪接一浪,2003年的歐洲熱浪奪去了近五萬人的性命;而俄羅斯的科學家則宣稱,2010年夏天的熱浪(最高溫達攝氏44度,而莫斯科也達39度),乃俄羅斯「一千年來所未見」。不用說,這些「持續高溫天氣」在我國亦正不斷肆虐和惡化,並對人民的健康和經濟生產帶來嚴重的影響。
哪麼我們還有多少時間以力挽狂瀾?科學家的研究顯示,我們絕不能讓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超過百萬份之四百五十(450 ppm),因為一旦超過此數,大自然裏不少「正反饋循環」(Positive Feedback Loops)將會發揮作用(如凍土全面融化釋出巨量甲烷),令情況一發不可收拾(英語中的所謂「reaching the point of no return」)。由於今天的這個濃度已達390 ppm,而濃度正以每年約3 ppm的速率增加,也就是說,我們最多只有20年的時間力挽狂瀾於既倒──亦即將我們的經濟全面「去碳化」(De-carbonization of The Economy)。
但事實上,我們絕對沒有20年時間這麼多!這是因為嚴格來說,上述的「450 ppm警界線」所涵蓋的不單是二氧化碳濃度,而是包括了其他溫室氣體如甲烷(methane)和氧化亞氮(nitrous oxide)等的「二氧化碳當量」濃度(CO2-equivalent concentration),而按照一些計算,這個濃度已經十分接近440 ppm這個數值。
在另一方面,愈來愈多的科學家開始對450 ppm這個經由「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所確認的「警界線」提出質疑。這是因為更深入的研究顯示,450 ppm這個水平實在太危險了。真正安全的水平應是350 ppm左右,亦即較今天的水平還要低40 ppm!(工業革命前期的水平約為280 ppm。)
既然已經超越了安全水平,為何世界仍未陷入大災難之中?你可能會問。答案有兩個:第一是災難其實已經在發生,只是氣候災變的展現形式不會像地震那樣明顯。這種相對緩慢的漸進式和累積性變化最容易使人掉以輕心意志麻痹,也正是為什麼「溫水煮青蛙」這個寓言是如此貼切的原因。至於第二個答案在上文經已提及,那便是自然界裏的「延滯效應」(Time-lag Effect)。在《喚醒69億隻青蛙》一書裏我用了不少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其中一個是堤壩出現裂縫而最終導致崩潰。簡單的道理當然是:待堤壩開始崩潰時才作出補救還有用嗎?
的確,所謂「未見棺材不懂流淚」,災劫未出現之前叫人作出預防措施往往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也如是。筆者數年前觀看由威爾斯(H.G. Wells)的晚年名著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改編而成的電影Things to Come,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不是片中對未來的描述,而是電影開首時數個劇中人在爭論一場歐洲大戰是否即將來臨。要知威氏的小說成書於1933年而電影完成於1936年,其時的西方人大都不信會出現一場席卷歐洲的戰爭,更不用說一場席捲全球的世界大戰。威爾斯不愧為獨具隻眼的科幻大師,因為在電影裏大戰果真爆發。至於往後情節如何,還是留待大家自己找小說或電影來觀看好了。
無獨有偶,在觀看這部電影的前後,我正在看錢鍾書所寫的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其中一個故事(名稱已忘了)講述一班好友在熱烈爭論日本是否真的會發動侵華戰爭(故事乃寫於日本侵華的前夕)。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錢氏以他令人折服的才情,透過了不同的角色人物道出了各種正、反兩面的觀點。令人感慨的是,那些不信戰爭會出現的觀點竟是如斯的情理兼備振振有詞……。人類真的要見到一排一排的棺材才懂得流淚?真的要見到屍橫遍野才懂得逃命?
現在讓我們轉過來看看,人類在面對如此浩大的災劫時,是否可以「將未來寄托於太空」。
從《流浪地球》說起三之二
本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