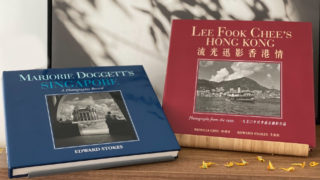大約20年前(即上世紀末),曾任新加坡外交官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出版了一本題為《亞洲會思考嗎?理解東西方的分歧》的著作。在作者看來,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陸,橫跨從日本、印度尼西亞到阿拉伯世界,涵蓋了伊斯蘭、佛教、儒教和印度教等幾大文明,人口占了全球的60%。(當時的)經濟總量即將在未來15年內超過歐洲和北美。但是,西方人對此無動於衷,他們對亞洲人的態度依然如故。作為外交官的馬凱碩因此有感而發,希望促成西方對亞洲的新思考。
今天,離這本書的出版20年過去了,不僅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日本是第三大經濟體,印度也正在快速崛起,但「亞洲人會思考嗎?」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如果說亞洲人不會思考,很多人必然會感覺到被「侮辱」,並且這樣說也不公平,因為如果說亞洲人不會思考,亞洲的變化又如何解釋?亞洲書寫了二戰以來世界上最成功的故事。
二戰之後,日本從戰爭的廢墟中崛起,之後是「亞洲四小龍」創造了公認的「東亞奇跡」,之後便是中國的經濟奇跡,現在全世界的眼光又落到了印度的崛起上。但問題在於,即使亞洲人有思考,也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即亞洲人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自己的話語權;即使愈來愈多的人對西方話語感到不滿意,但在行為上一切依然以西方話語為依歸。
馬凱碩的《亞洲會思考嗎?》想給西方讀者傳達出「亞洲會思考」這樣一個信息,希望西方對亞洲事務做重新思考。如果那樣,這本書的書名應當為《西方會思考嗎?》而不應當是《亞洲會思考嗎?》。但從現實來看,這本書的書名最也恰當不過了,因為現實的情形是:不會思考的不是西方人,而是亞洲人本身。
這本著作在西方所產生的影響遠遠大於其在亞洲所產生的影響。這個事實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西方人對亞洲不是不會思考,而是經常做「錯誤」的思考。當代亞洲的崛起是西方人最為關切的事情,無論是日本的現代化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都在西方得到相當充分的研究,更不用說對當代中國崛起的研究了。
同時,對亞洲事務的關切也充分反映在西方諸國對亞洲政策的變化上。相比之下,亞洲人本身除了照抄照搬西方話語之外,對亞洲經驗的「知識化」可以說沒有什麽實質性的貢獻。正因為如此,直到今天,有關亞洲的話語仍然為西方人所掌握。
所以,問題的本質不在於西方對亞洲事務的「不當思考」,而在於為什麽亞洲人有豐富的實踐但不會思考。
一句話,亞洲還沒有脫離西方的「殖民」,或者說西方仍然在「殖民著」亞洲。
亞洲的兩個殖民階段
就殖民來說,亞洲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近代以來的「被殖民」階段,即西方強權的殖民地主義階段。在這一階段,大多亞洲國家被西方國家所打敗,淪落為西方的「殖民地」。即使中國也成為了毛澤東所說的「半殖民地國家」。所要強調的是,這個階段是「被動」的殖民。
第二個階段即二戰之後的「主動」的思想殖民階段。在這階段,通過亞洲各國的反殖民運動,物質意義上的殖民地消失了,但思想上的殖民地主義根深蒂固,不僅無意識地存在下來,而且變本加厲。在「被動殖民」階段還存在著各種形式的抵抗,但在「主動殖民」階段,不僅毫無抵抗的跡象,更有自我「摧殘」現象的發生。
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這種情況存在已久、產生的原因也很覆雜,但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是可以觀察得到的。
首先是近代以來的很長時間裏,亞洲國家力量弱小,無法改變西方持有的亞洲話語權。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也是第一個打敗歐洲國家(俄國)的亞洲國家。日本曾經試圖通過把歐洲列強趕出亞洲的方法,確立自己的亞洲霸權,即建立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但日本帝國主義的做法不僅沒有幫助日本確立亞洲霸權,其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更是給亞洲國家帶來了戰爭。
二戰之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被「吸收」進西方陣營。儘管日本戰後很快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日本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完全的主權國家,無論內政和外交深受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制約。日本之後崛起的亞洲「四小龍」也基本上屬於西方陣營,無法改變現狀。進而,為了讓西方接受他們,這些經濟體往往采用「投降」政策,把自己偽裝成西方,即盡量強調其和西方的雷同之處,而不敢張揚其和西方的不同。
當然,其中也有「持不同意見者」,主要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李光耀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亞洲價值觀」,可以視為是亞洲「異見者」的政治宣言。這些「異見者」還包括當時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和日本一些政治人物。
在學術界,也有不少學者做過努力,把「亞洲價值觀」學術化,試圖來解釋和敘述亞洲的成功。不過,「亞洲價值觀」不僅遭西方的圍堵,而且也遭到亞洲那些追求西方式民主的政治人物的批評,主要來自韓國和台灣,因為這些社會當時正經歷所謂的「第三波民主浪潮」。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亞洲價值觀」便在大眾媒體上消失了。
第二個原因是亞洲一些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對西方式民主自由的信仰和追求。他們簡單地把西方國家近代以來的強大和亞洲國家的落後歸結為民主與自由,即前者實現了民主自由,而後者沒有民主自由。亞洲很多追求西方民主的自由主義者,實際上並不知道西方民主是如何產生、如何運作的,但一旦民主自由成為了他們的信仰,他們無論怎樣也不會對西方產生一點點懷疑,他們的選擇是全盤接受。
這也很容易理解,只有那些理解西方民主的政治人物(例如李光耀),才會對西方制度持批評的態度。不管是什麽原因,的確一些亞洲國家和社會建立了民主體制。不過,盡管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這些亞洲民主並非西方式民主,這些社會也要偽裝成為西方民主,盡量不站在西方的對立面。
日本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並不符合西方政黨輪替的民主概念。西方學術界對日本民主一直持批評態度,但這種情況並沒有出現在西方政界,這個事實也說明日本「偽裝」的成功。
第三,利益和話語之間的衝突。亞洲這些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在整個冷戰期間屬於西方陣營,它們各自從西方陣營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它們的發展更離不開西方陣營。在這樣的情況下,亞洲社會出於對實際利益的考量,不想塑造自己的話語權。很顯然,一旦具有了和西方不一樣的話語,就很容易主動地或者被動地被西方視為「對立面」。一旦這種「對立面」形成,就必然會影響這些社會在西方主導的體制內追求自身的利益。
亞洲國家之間無共識
第四,各種衝突阻礙著亞洲國家之間的共識,沒有共識,自然就沒有亞洲話語權。亞洲是一個多文明、多文化的地區,並且各國之間、不同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也相差甚遠。多文明和文化使得它們之間少則缺失共識,多則導致沖突。這種情況既反映在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大國之間,也存在於東南亞各國之間,或者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
即使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東北亞國家之間,也因為歷史和戰爭的原因而無法達成有效的共識。亞洲國家之間的衝突往往賦權西方,使得西方總能找到亞洲國家之間的「矛盾」,從而在殖民地結束之後繼續主導亞洲事務。同時,也是因為亞洲國家之間的沖突,使得一些亞洲國家主動尋求西方的幫助來對付另一些亞洲國家。這種現象自近代以來一直很為普遍,存在於整個東亞(東北亞和東南亞),更不用說包括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在內的亞洲了。
第五,更為重要的是亞洲教育市場的殖民地主義。近代以來,亞洲精英人物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接受西方教育的,另一部分是從內部成長起來的。但無論起源如何,他們當中大部分都接受了西方價值觀。二戰之後,亞洲國家獨立了,但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系統並沒有獨立。一些國家進行了「去殖民地主義」運動(例如新加坡),但教育系統的獨立性也是有限的。更多的國家則是主動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系統。
這種情況的存在不僅僅在於西方教育系統在客觀上較亞洲先進(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更在於亞洲國家沒有自己的信心和能力,把自己的發展經驗提升成為以亞洲為經驗基礎的社會科學。盡管亞洲國家的學者也提出了「東方主義」的命題,並且也一度盛行,但無論是「東方主義」還是後來的「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理論都是解構型的,而非建設型的。
就是說,這些理論僅僅抱怨西方話語霸權,但並不能成為建立亞洲話語的理論基礎。這種情況直到今天仍然不能改變。亞洲國家還沒有能力發展出自己的評估系統,一些以西方為標準,甚至比西方更為西方。自然科學還說得過去,但社會科學則令人擔憂。例如,較之西方,亞洲的教育市場大多由官僚主導,官僚主導的教育市場為了在國際競爭中取勝(主要是排名),對本國的教育系統進行主動的「殖民化」,一切以能夠在西方學術雜志上發表文章、能夠發表西方式的文章為最終依歸。這都使得亞洲教育市場儼然是西方市場的內在一部分,沒有看到任何獨立的跡象。
西方教育市場的強大在於其思想,而非思想的學術表述方式。而亞洲社會則以極端機械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的學術表述方式,在這個接受過程中,亞洲的思想也不知不覺地被西方「社會化」了。
因為這些,今天亞洲只有發展、沒有思想的局面並不難理解。這種局面也使得亞洲國家處於一種極其難堪的狀態:盡管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不能解釋亞洲經驗,但人們仍然不得不用西方概念和理論來解釋自己。今天中國的狀況更加令人擔憂。中國實在太大了,不能像早些時候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偽裝」自己。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一點也不想「偽裝」自己。
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做法剛好相反,其他亞洲國家強調的是自己和西方的雷同,而中國張揚的是自己和西方的不同。不過,中國並沒有能夠讓西方(甚至亞洲國家)理解和接受的「故事」。這使得今天的中國和西方(及那些接受西方話語的非西方國家)處於意識形態的對立。
當然,未來印度也有可能會面臨同樣的情況。盡管印度到目前為止,仍然被西方視為最大的民主,但隨著其發展,印度和西方的衝突也只是時間問題,而非可能性問題。如同中國,一個龐大的印度也很難「偽裝」自己。
「亞洲」的概念本來就是西方殖民地的產物,很多亞洲國家也淪落為西方的殖民地。但如果亞洲不能從思想上獨立出來,如果繼續沒有自己的思考和思想,一切以西方為依歸,前途很難說是光明的。搞不好,亞洲很難避免「中東悲劇」,即被西方「分而治之」。今天,當亞洲成為世界地緣政治中心的時候,這種危險性也是史無前例的。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