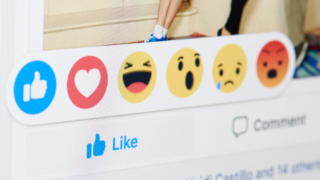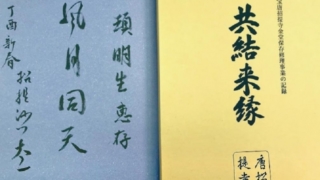龍應台先生的文章向來得內地網民垂青,可謂嬉笑怒罵,無奇不有。日前先生引用了韓晗先生一文,旨在慨嘆中華文化江河日下、禮失而求諸野。我既同意,亦不同意。誠然,我華夏經新文化運動及文化大革命蹂躪後,有如風中殘燭,禮法早已蕩然無存。加之西洋崛起,而全球化湧現,促西學東漸,使我國於其推崇有加,洋務運動自此不迭,坊間民眾更沉溺難已。自始齔之年,國人習西方之語言,讀西方之書籍,承西方之價值觀。我們眸子裏,一切西方論調彷彿盡皆理所當然。且大數據時代及至,群眾與書本脫節、聖賢書早拋諸腦後。古來文教尚興,書生坐而論道、市井小民恐亦出口成章,今鮮見其光景。姑莫論文學素養,若問四端五常,眾人也只能瞠目結舌,以笑遮醜。當今社會受害於所謂時代洪流,儼如文化沙漠、病入膏肓,情況堪憂。
然而,古往今來,群眾目不識丁實乃稀鬆平常。梁實秋有云:中國社會,知識一直未能普及。咬文嚼字,是少數人的玩意兒,古來尤甚。我認為並無不可。舞文弄墨,或抒情,或頌世,或愚民,從乃士大夫的特權。昔時非士即農,雅俗之分,即士農之分。雖讀書非上層社會獨有、農學而優亦可仕,但書香門第的公子成才終究比寒門出貴子來得容易;前者得高人授而諳道,後者則需私窺門徑。話及「公子」,此公子非彼公子。華夏之「公子」,乃官僚貴族(即士族)之子的稱謂,有見「王孫公子」;西方資本主義下之「公子」,多指富家巨室之後。當然,王孫則富,富卻未必為王孫。王孫士族,就是精通文字的少眾。文字是藝術,是美學,是上層階級的玩意兒。既然如此,就不應妄求大眾通鑑。藝術曲高和寡,而擺放人前,難道人人都懂梵高之作?大多人看罷拍拍屁股便溜,知音從來少數。若為求知識普及而俗化文學,於簡體字之例又有何異?捨本逐末,亦有違先生本意。有些事物可隨時代變遷,有些則不能為了迎合大眾而降格以求。藝術旦遭外來壓力而自我整肅,還算是藝術麼?我寧可文學少些人賞識,也不願削足適履。若再多來一個陳獨秀,提出什麼「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及「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華夏文化的一點殘羹也要燃燒殆盡了。
「武漢加油」此話旨在激勵全國人民
「武漢加油」實無傷大雅。要道不落俗套,台灣的「用愛發電」也不見得雅緻。通俗易懂,只要非不可耐,便無不妥。「武漢加油」此話旨在激勵全國人民,實用為先。識文學者寡,若政治標語過於艱澀,便無法收效。管治之道並不可處處以文學論之。或這般說,雖在位者通曉文學,但其勁道得當,收放自如,乃至中庸。故治國者必為文人,文人卻非皆會治術。
其實,「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帶一路四中全會」不失為創意之作。民間作自娛之用,韓晗先生也不必過於拘謹,當可一笑置之。兩位先生又冷嘲熱諷,歎群眾縱自幼習文,年長後卻仍擠不出半點墨來、情急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還不如「我操」兩字來得快。既是如此,先生當知道知識實無法普及。逼迫群眾品高雅趣味,難矣哉。文學是少數人的玩意兒,自有其原因。見社會俗民推廣滿口粗言即隨性的劣文化,由之即可,何必動氣?三教九流當有其模樣,難道先生奢求人人都是賢才君子嗎?若道官樣文章中的修辭貧貧猶如念經、直似小學生水平,或文壇崩塌、絕後可期,倒確實令我輩心焦如焚。這歸咎於我首段提及到的種種禍害。
見及內地網民於先生文章的留言浩如煙海,縱水平參差,也令我嘆為觀止。我既訝異於其壯觀景象,亦暗暗竊喜。畢竟,只有龍應台先生的平台方能牽起如此迴響、使人討論文字與文化,評論也見學養。文下留言竟像似文字,我實在欣慰不已。現網絡發達,不成器的言語俯拾皆是。且別說有否文氣,句子或殘缺不全,或語病連連,文不成文,內容更無營養。話說到底,文盲處處實屬等閒,毋須強治。只要我們的樑柱不失宗師泰斗,饒宗頤、金庸及董橋等後繼有人便可。自古以來,能者居少,民族成就也從來是寥寥豪傑為整體立下的豐功偉業。駕者與輪子,不過是各司其職。所以群眾通俗,又何罪之有?
(倭國贈我華夏八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既然國民啞然,我就代為回贈之:「漢夷無疆,雲星共賞。」此謝禮既顯大方,亦展現大國威儀──「我漢乃華夏正統,你不過是番邦夷狄。」最後押韻,示意話及漢語,仍乃我中國技高一籌。)
作者簡介:廖浩鍇(Ho K.V. Liu),字抱玉,號帝江、驚鴻,筆名浩林。吟遊詩人、專欄作家、《超級菁英論》作者、英國留學生俱樂部COLUMNAE百岳以及香港青年學生組織莘火言碑創會會長及召集人。現為大學生,尤痴愛中國文學,喜好創作詩詞歌賦;最喜愛自己的文學作品為《香冷兮歌》。自詡為荀子之後,理想是匡正禮樂,扶持社稷。人生第一本拙作為《士子論道—兩鴻鵠雲遊邱壑》。目標是成為政治理論家、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並成為尼采《超人論》中的第一人。